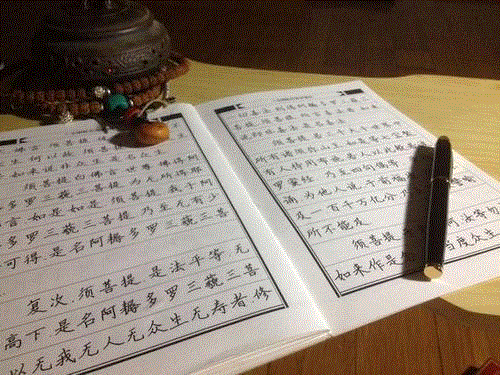论《维摩诘经》和净土思想在中国中古社会之关系
发布时间:2023-07-10 09:31:20作者:药师经全文对于《维摩诘经》在中古时代社会和精神生活方面之重要性早以是学界的共识。虽然以居士维摩诘为主角,以提倡不二法门为宗旨的经文一向被认为是最受到中国士大夫阶层重视的经典,但其影响的层面在不同时期都具有不同之特点,这里我要着重探讨是此经自中古以来和净土思想的种种关联以及从中所反映出来的中国佛教在唐宋之际的某些转化。而在涉及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行解释一下此经从南北朝到隋唐期间其影响的发展轨迹,以为我们的探讨提供一个背景。
从六朝到唐宋,《维摩诘经》影响的特点概括起来大致有两个。第一,此经的文本通过不断的传译而引入中土,几乎从其进入中土的一开始,他就成为僧众用来劝导世俗人士,特别是统治阶层中之文化精英分子信仰佛教的利器,这可以说是此经能迅速居于中古佛教文化之中心地位且能长期受到欢迎的基本要素。此经所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系列的观念,还是一种可资模仿的修行方式。维摩诘以俗人身份而与佛陀并驾的描述给与一向对自我的道德和文化优越深有自信的士大夫阶层以极大鼓励。但这一影响绝不只是单向的。中古的世人也不断以此经的理论和维摩诘的修行方式来向一些为佛教僧徒所维护的理论和实践提出质疑甚至挑战。这一点在隋唐时期关于僧人是否应该向君主及父母礼拜的论争中有清楚的显示。所以虽然佛教僧侣在倡导世人模仿维摩诘实践的同时,又不得不对维摩诘只是以俗人面目出现的菩萨之一特性加以强调,从理论上对一般人实现维摩修行法的可能性加以限制。《维摩诘经》的这种双重特性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出家与在家矛盾的一种反映。
第二个特点就是此经的影响自南北朝以来经历了一个不断世俗化的过程。虽然在六朝的前期,玄学和清谈的盛行是此经得以受到重视之关键,但随着此经之普及,其影响早已越出了义理辨析的范畴而进入宗教实践和文化的各个层面。进入隋唐时期,此经的普及性可以说有增无减。《维摩诘经》与其他许多重要经典的不同之处在于其独立的特性。他并未如许多其他经典那样和某一学派产生直接之关联。(禅宗可能算是例外)所以此经之影响往往不受教派之盛衰而盛衰。

依据唐代的史料,我们可以看出《维摩诘经》在文化教育中地位的显着变化。就士大夫阶层而言,此经已成为和三礼、文选一样属于最为基本的读本。这一点从唐代文人的写作中大量引用此经的文句和典故可以得到充分证明。有些学者以这方面的例证来强调士大夫对于《维摩诘经》本身的信奉,这一解释当然不无道理,但却忽略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隋唐以后,《维摩诘经》已由一种思想前卫,能为当时哲学思辨和宗教实践注入新血液的佛典逐渐转化成一种可以说是普及性的,可用以了解大乘佛理的入门读物。绝大多数的士大夫研读此经的主要动机恐怕未必全在于对其义理的着迷和对于维摩诘生活方式的钦羡,更多的是希望能以此来掌握佛教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词句以应付不同场合之需要。此经篇幅的短小,情节之生动,译文之美妙,以及义理之易于了解皆使之适应了这种需要。《维摩诘经》作为唐代文化系统之重要组成的这一特点可以说进入宋代还持续不断。南宋楼钥在称赞陈瓘之(有门颂)的同时评论说:「近世士大夫用力不及前辈,秖如学佛,仅能涉猎楞严、圆觉、净名等经,及传灯语录,以资谈辨。」(《佛祖统纪》卷四十九,大正藏2035/442C)正是此种「以资谈辨」的心理,使一般的土人都以熟悉此经内容为要务。
而这一特点也同样出现在佛教界。总起来说,以为《维摩诘经》作注的方式来阐发新思想的倾向在唐代确实明显的衰退了。从东晋到隋代,此经的注疏不仅层出不穷,而且往往是新学派用来阐发其理论的代表性作品。尤其到了六朝末期和隋代,由于净影慧远,吉藏、和智顗这些重要人物的自觉努力,以及如隋炀帝这样的统治者的全力推崇,《维摩诘经》的注疏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巅峰的状态。但进入唐代之后,除了窥基依照玄奘之新译本而作的注疏之外,几乎可以说再也没有在义理的阐发上具有重要价值之研究了。流行于这一时期的注疏,诸如道液的《净名经集解关中疏》和《净名经关中释批),也只是以援引僧肇、智顗的旧注为主。对于此经义学研究兴趣之衰退还可以由另一重要的例子得到说明。在初唐,玄奘便重新翻译了《维摩诘经》。玄奘重译此经的动机值得注意。Etienne Lamotte在其法译之《维摩诘经》的前言里就指出,玄奘的重译,在遣辞造句方面为精确传达该经的旨意作了最大的努力。可以说完全没有被他本人所追随的唯识思想所影响。明证之一就是在此经经文中所出现的alaya一辞,玄奘并未以他在翻译唯识着作时所用的「阿赖耶识」来表示,而谨慎的采用了「摄藏」以表示其独特之涵义。既然我们可以排除玄奘有以通过重译此经来阐发其唯识思想的可能性,那么就不难推测他重译的主要原因应该只是对众多前译的不满,而此经在当时的普及应是使他感到有重译之必要的关键。对此他的弟子窥基作了明确的说明:
今此经者……以经六译。既而华梵悬隔,音韵所乖。或髣佛于遵文,而槽粕于玄旨。大师皎中宗于行月,镜圆教于情台。维绝纽而裕后昆,缉颓纲以为前范。陶甄得失,商榷词义,载译此经。(《说无垢称经疏》卷一,大正藏l782/993a)

就精确而言,玄奘之译本确实超过了罗什的旧译,但其译本的实际影响却极为有限。连当时佛教界都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重译在义学上之意义,更不用说一般的世人。相对于义学研究的衰落,《维摩诘经》在寺观教育中的普及性却大大超过前代,成为僧侣学习佛教教理的起点。在六朝期间,善讲此经往往是一些一流大德的专长。由唐至五代,更普通的情况则是此经成为僧人在接受寺院教育时,最先接触到的几部经典之一。许多僧人在他们年幼时,即开始记诵和学习此经。这几乎成了出家前准备阶段基本训练之一部分。这一现象可以在《宋高僧传》中找到大量的例证。
虽然对于此经文义之研究,自唐代已不再如前代之活跃,但其理论的影响却不因此而减弱。如果说在六朝时期,《维摩诘经》的不二理论和在家修行的主张是其最为引人注目的方面,那么在唐宋时期他对于佛学界的影响就着重表现在对于禅宗思想的启示和与净土理论所造成的冲击紧张关系。而这两方面的影响又可以说是紧密关联的。而这些新的影响,一方面是当时佛教思想发展本身应运际会的结果,另一也再度体现出《维摩诘经》在中土社会中自身的特点。对与本文所要探讨的第二种关系,即此经与净土理论的关系,必须从此经本身关于净土理论的分析开始。
《维摩诘经》中译,特别是鸠摩罗什之译本,对于中土净土理论有至关重大的影响。《维摩诘经》阐述净土意义的地方主要有三处,分别在〈佛国品〉(或序品),〈香积佛品〉和〈见阿众佛品〉中。用吉藏的话说,也就是「庵园明释迦佛土,方丈辨香积佛土,后会明无动佛土」。(《净名玄论》卷七,大正藏l780/902c)尤其是第一品〈佛国品〉(或序品),是经中对净土看法之集中表述。此品强调佛土之净秽不在于佛土之间在性质上的差别,而在于心净与否,所谓「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这一斩截之论断为中土「唯心净土」的思想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础。而重视在秽土中得菩提的思想环绕着整个经典。比如在〈香积佛品〉中,强调在娑婆世界,即秽土中的菩萨一世饶益众生,多于在作为净土的众香国中菩萨的百千劫行。而且娑婆世界有布施、净戒、忍辱等十事善法,为其他净土所无。这一看法明显和《无量寿经》「此界一日一夜修道,胜余佛土百年」的说法有差异。在见阿閦佛品中又说明维摩诘为化众生,而自作净土妙喜世界转生秽土。《维摩诘经》的净土义是其不二法门的一种表现,但这正与隋唐之际强调「厌患娑婆,愿生净土」的净土信仰的理论形成根本的差别。此经所谓的「心净」(citta-parisuddhi)有其特定的、建立在般若思想基础上的涵义,也就是「法眼净,知有为法皆悉无常者。国土秽而可净,净而复秽」(吉藏语)。
我们在强调《维摩诘经》「心净土净」理论的同时,也应主要到此经净土观念中内在一些紧张关系以及可以和净土信仰相融的成份。日本学者藤田弘达等,就注意到了「净佛国土」和「极乐净土」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他指出,严格来说,一些大乘佛典的中译本中的净土用语,所指的只是净佛国土(Buddhaksetraparisodhana),而并不具有后来净土宗所提倡的净土之涵义。而大乘佛经又显示出「佛国土」有从无形的净土向有形的净土转化的趋势。(见藤田氏《原始净土思想?研究》岩波书店,1970,页507~516。)而这一趋势在《维摩诘经》中已经表现出来了。比如当释迦向解释严净佛土的意义时,他所指的净土的实质是无贪无痴的无形净土。但当他为了让使怀疑此论之舍利弗相信,还特意「以足指按地,即时三千大千世界,若干百千珍宝严饰,譬如宝庄严佛、无量功德宝庄严土」。这样一来,便无疑提供了可以以有形的、外在的净上来表示无形净土的例证。《维摩诘经》中同时出现了以众香国以及妙喜世界等在形式和性质上都与西方净土极为相似的净土世界,而且维摩诘本人也是从妙喜世界转世而来。虽然这些情节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配合经文中具体章节所涉及的教义而设计,但毕竟为承认有形净土的存在提供了空间。

同时虽然《维摩诘经》为唯心净土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这一「心净」的过程却并未能脱离他力的相助。释迦和维摩诘的教诲和不可思议之神力都是他力救度的表现。而且经中也并没有排斥往生净土,在阿閦佛品里,当信众目睹妙喜世界之严净而渴望往生其土时,「释迦牟尼佛即记之曰:『当生彼国』」。所有这些因素使得《维摩诘经》的义理和以强调他力重要性之净土信仰有条件加以调和。禅宗在吸取了《维摩诘经》「心净土净」观的同时,却并未强调他力的作用。《六祖坛经》中有一段有名的有关净土的对话,清楚的显示出和《维摩诘经》结构之相似和区别。当慧能的听众向他询问有关西方净土的存在之问题时,慧能说:「慧能与使君移西方刹那间,目前便见,使君愿见否?」当在场听众表示愿意之时。慧能便突然说:「唐见西方无疑」当大众错愕,不了解慧能为何如此说时,后者便阐述了净秽在心而不在国土的禅门净土观。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坛经》中这一段是模仿《维摩诘经》中释迦显现净土一段而来的(见赖永海《中国佛性论》上海,1988,页263~265),但两者之间最关键的不同在于慧能并未如释迦那样,向他的信众显现出有形之净上来。这一区别也正是以强调通过自力而证悟的襌宗和依然重视佛陀他力作用之《维摩经》的一大分野所在。
「心净土净」的理论在隋唐之际开始对日益流行之净土信仰形成理论上的压力。我们虽然不必过于夸大这种压力。因为首先义理之辨析并不是净土信仰的中心,同时义理上的分别也未必能对在实践层面上的融合造成困扰。但是《维摩诘经》一向在中土居土佛教的实践中具有指导性地位,同时「心净土净」也正是当时盛行之禅宗用以建立其理论体系,并对净土信仰加以大力抨击的出发点之一。从这两方面而来的压力更使净比僧人无法对这些义理上的矛盾加以回避。而我们现今得以了解的隋唐以来的净土思想之文献也充分说明他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心净土净观是绝大多数净土理论的典籍所关心的课题。这种重视不仅是因为义理本身的不同,也是《维摩诘经》在中古世俗社会中所具有的广泛影响所引起。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的士大夫会对这些理论的差异无所察觉。几乎可以说,如何化解此经中心净土净和一般净土信仰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将其容纳到净土思想的系统之内的努力贯穿了隋唐以来净土思想发展之全部历史。
净土信仰的僧人首先要回应的最为关键的两个问题是:第一,既然佛土之净化完全可以通过心净来取得,那么为何还需往生西方?第二,按照《维摩诘经》之义理,既然在现世秽土中可以取得在其他净土世界中所不能之成就的功业,我们为何还要选择往生西方净土?对于提倡西方净土信仰的僧人而言,他们解答这两个问题的基本方法是强调能从秽土中体悟到净土义需要有超凡的资质。维摩诘是大士,自然可以完成这一过程,而凡人则万万不可。
对于心外无法,所以不必往生的论调,道绰在《安乐集》中便指出:
但法性净土,理处虚融,体无偏局。此乃无生之生,上士堪入。……自有中下之辈,未能破相,要依信佛因缘求生净土。虽至彼国,还居相土。若摄缘从本,即是心外无法,若分二谛明义,净土无妨心外也。(大正藏l958/8c~9a)
对于第二个问题是否在娑婆世界,也就是秽土可以成就比在西方净土更为难能之善业的问题。道绰在《安乐集》中也特别作了解答,他说:
若身居不退已去,为化杂恶众生故,能处染不染,逢恶不变,如鹅鸭入水,水能不湿,如此人等,堪能处秽拔苦。若是凡夫者,唯恐自行未立,逢苦即变,欲济彼者,相与俱没,如似逼鸡下水,岂能不湿?是故《智度论》云:「若凡夫发心,既愿在秽土拔济众生者,圣意不许」。(大正藏,1958/9a~b)
而这一看法也绝非专注于提倡净土信仰的道绰才有。窥基在其《西方要决释疑通规》中对此也有同样的议论:
善逝弘规,靡不存益。各随一趣,理不相违。何者,修行之机,凡有两位,未登不退,难居秽土,欲修自行,多有退缘。违顺触情,便生忧喜,爱憎竞发,恶业复兴,无法自安。还沉恶趣。若也修因万劫,法忍已成,秽土堪居,方能益物,既成己行,已免轮回,十事利他,诸方不及。依报精华,众具莫亏,所须随念,既无乏少。施欲何人,自余九事,准斯可委。所以自之不退,住此无妨。广业益他,胜诸佛国。当今学者,去圣时遥,三毒炽然.未能自在,若生净土,托彼胜缘,藉佛加威,方得不退。(大正藏l964/105a)
窥基并不否认在秽土可以成就比在西方净土更大的善业,但这只是像维摩诘那样的大士才有可能,凡夫是不能有所企盼的。
由《维摩诘经》还引起了如何能往生的讨论。《维摩诘经》强调净土的前提是心净,那么被妄见所缚之凡夫又如何能向净土僧人所称的那样往生西方呢?对此怀感在他的《释净土群疑论》中认为《维摩诘经》之观点是就净土的究竟意义,也就是第一义谛的立场上加以说明的,而往生西方则是依靠已心净之佛的外力而得,是在世谛因绿的范围之内,所以两者不相矛盾。正如《维摩诘经》所说的,心净之菩萨能为其他有情显现无漏净土。(大正藏l960/34a~b)在这一点上,他和道绰是一致的。
响应道绰等人这些主张的人士很多,比如宋僧元颖在其《净土警策序》中说:「世人或没于苦海,则自甘其分,或迷于富贵,则自逞其得,而不知生生死死于瞬息间久矣。至有谓心净佛土净空身即法身,及大期忽终,无所安立。」(《乐邦文类》,大正藏l969/7173c)晁说之也批评那些一味提倡唯心净土的人说:「但言我能心净,孰非净土,似能为维摩之书,而身实天魔之民也,岂不可重惜哉」。(见《乐邦文类》所载《净上略因》,大正藏1969/209a)又如《莲宗宝监》载寂室大师的议论:
或闻说净土,必曰净土唯心,我心既净,则国土净,何用别求生处。寂室曰:且《维摩诘经》中云,如来以足指按地,见娑婆国土,悉皆严净,而众会不见,唯螺髻梵王得知。今之说悟性者,能如梵王所见净土否?况汝居卑室陋室,必羡之以大厦高堂。是则口唱心净土净之言,身批秽土苦恼之缚,其自欺之甚也。
通过以上简要的讨论,我们可以了解到隋唐以来的追随净土信仰的佛教徒对调和《维摩诘经》中「心净土净」的唯心净土说和往生极乐之间的矛盾之主要途径。我们必须看到的是虽然这一理论上的问题常迫使净土信仰的倡导者以调和的方式来为往生作辩护,在实际倡导净土信仰的层面,僧人却可以自由的运用此经所具有之感召力来辅助其净土信仰。比如唐代净土宗的着作里引用《维摩诘经》的文字是很常见的,而且这种引用有时甚至不顾经文是否和该着作的理论一致。这一点在善导的作品中非常明显。在他的《念佛镜末》中提出念阿弥陀佛可以速成佛果,远远超过坐禅看心作无生观。他特别引用《维摩诘经》「譬如虚空造立宫室,终不能成」之语,认为无生即是无相,而无相即是虚空。这是就字面而作的牵强解释。在其《劝进念佛之门》中又说:「修道之人,要勤念佛。《维摩诘经》云:『欲除烦恼,当须正念。』」(大正藏,1966/122b)这里所引用的词句,出自〈观众生品〉,对于「行正念」之意义,经文强调是「行不生不灭」,与善导等所提倡的念佛无直接的关联。但这却开启了将念佛与心净相融合的过程。明代的袁弘道就直接了当的说:「夫念即是心,念佛岂非心净,心本含土,莲邦岂在心外」。(《西方和论》卷一,大正藏l976/390b)
除了引用《维摩诘经》语句为净土义理张本之外,法照在他的《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中更包括了《维摩赞》,显然把对维摩诘的颂扬列入了净土轨仪的关键部分。706年,怀晖在长安创立了着名的香积寺,怀晖是净土信仰的核心人物善导之弟子,香积寺在唐代始终是净土信仰的重要寺观,而其寺名正取之于《维摩诘经》之〈香积佛品〉。
随着净土信仰之普及,《维摩诘经》中所提到的佛国净土也影响到了净土僧人对于净土性质的认识和分类。按照净土信仰的理论,《维摩诘经》中所出现的净土在性质上是不相同的。净土有实土和权土,或报土和化土等许多种分别。在《华严合论》中,活跃于开元时期的作者枣柏大士李通玄列出了十种不同的净土,其中七种,包括《维摩诘经》〈佛国品〉中释迦所显示的净土和西方净土在内,都属于权土,也就是佛陀为启发众生而实施的权变的结果。(见《莲宗宝监》卷3,大正藏,1973/318a~b)而《维摩诘经》所强调之唯心净土则是实净土。枣柏此种分类显然颇有影响,特别是未将西方净土列为实土的论点,值到清代以来还受到净土僧人悟开以及印光之反驳。(见悟开对枣柏论之评语及印光《净土决疑论》)另外迦才在其《净土论》中则将妙喜世界当作常随化净土,而在〈佛国品〉中释迦为教化众生而显现之净土属于无而忽有化净土。(大正藏1963/84b)迦才同时又以类似判教的方式,对净土加以分别,列为三等。他认为东方妙喜世界属于下净土,原因主要是男女相杂,西方极乐世界是中净土,因为二乘相杂,而众香世界则是上净土,因为无二乘。凡此种种,无法在此一一列举。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中古以来的净土信仰一向被认为是佛教在中土世俗化的重要表徵,但就解决《维摩诘经》理论与其所产生的矛盾而言,净土僧人却一再强调《维摩诘经》理论适应的有限性,维摩诘只是可以钦羡,却难以模仿。虽然这种强调并非自净土僧人开始,他们却是始终坚持这一基本法则以解决《维摩诘经》理论所引起问题。同时他们也用。把《维摩诘经》的理论放在实相的层面,和以实践为主的净土往生信仰相分隔,这可以说是《维摩诘经》在中土社会所具有的双重性格的继续和发展。当禅宗将《维摩诘经》中平等无碍的思想发挥到极至的同时,净土僧人却否认了此经在实践上的普遍性,而大力贬抑凡人觉悟的能力。这从维摩诘信仰的发展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但这从宗教实践的角度,也是用以避免世人以维摩诘的模式,以心净为藉口而忽视佛教的修行,所以其用心不能不谓良苦。所以这一努力,可以说也为宋元之后禅净的汇合作了先导。最后我们还应该提出的是,中古以来,贵族士大夫不仅是维摩诘信仰的支柱,也是居士佛教的核心。净土僧人对维摩诘修行模式的可行性加以否定,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古知识阶层对佛教实践的认识,这不能不是我们应当关心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