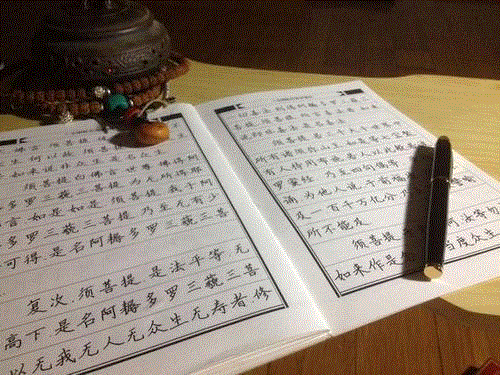高明道老师:佛门行者的「课」指什么?
发布时间:2024-09-20 01:32:55作者:药师经全文
高明道老师:佛门行者的「课」指什么?
中国佛教寺院里,僧众早晚固定都有「课诵」,甚至也有优婆塞、优婆夷在道场跟着师父们一起参与抑或自己家里「作早晚课」。这在华夏佛门是三宝弟子集体行持及个别用功的普遍现象,但兹所谓「课」到底如何理解才对,恐怕未必都很清楚。例如《汉语大词典》将「课诵」解释成「课读吟诵」1,质言之,把「课」、「诵」拆开来,然后分别用「课读」与「吟诵」两个动词来说明。然而这样作,不仅没有解决问题,且更带出进一步的疑惑,因为一查,就发现该词典在「课读」下列出两个义项──「进行教学活动,传授知识」和「接受教育,学习知识」2──,使得读者陷入一个新的谜:「课诵」究竟指涉知识的传授还是知识的学习?再加上《汉语大词典》的书证都很晚,不是清朝以后的3,就是「课诵」下金朝元好问《学东坡移居》诗之二的「谁谓我屋小,十口得安居。南荣坐诸郎,课诵所依于」,字里行间灌输「宋代以前并没有『课诵』」的概念。读到这边,也许有人质疑说:《汉语大词典》是大陆 80 年代的产物。在没有宗教常识的大环境里,编纂者对释氏的文化自不甚了解,所以词书的内容实际上只是反映一个历史悲剧,并不能代表普遍的模糊状态。此论点多少有点道理,不过问题是:佛教内部本身也不见得比较清楚。例如《香港佛教》杂志第 584 期(2009 年 1 月)登了上海云翔寺慎独法师《略说寺院早晚功课》一文,开场白中就说:「朝暮课诵是指汉传佛教寺院每日于清晨与入暮时分所举行的例行课诵,……。由于僧人在念诵时能够获得功德,所以课诵又称为『功课』。」4这样的解释很可疑,因为要用单音节的词指「功德」,一般都是「福」,似乎没有任何地方有独自的「功」代表「功德」,不过这样望文生义的发挥也非慎独法师的创举。之前,在中国佛教协会编的《中国佛教仪轨制度》(2003 年)里早就有王新的一个题为《课诵》章节,开宗明义地说:「课诵是佛教寺院定时念持经咒、礼拜三宝和梵呗歌赞等法事,因其冀获功德于念诵准则之中,所以也叫功课。」5无疑慎独法师以此为底本。他之所以加以改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冀获功德于念诵准则之中」不容易明白。其中「准则」这突如其来的表达,依笔者初步判断,渊源于兴慈法师 1921 年修订刊行的课诵本《示要》:「功课者,儒所谓:事有成效曰『功』,试计程限曰『课』。又谓:定治事之课程以期成绩者曰『功课』。然我释氏之言功课者,谓计功于三宝之程度以为日用之准式也。」6此番说解也不好懂。兴慈法师「儒」的定义是根据怎么样的文献提出的,笔者目下还没有办法确定,不过最起码针对「释氏」的部分可以从上下文判断「日用之准式」指「功课」的实质作用,而至于字面上的剖析,兴慈法师则以「课」为动词,将之翻译成「计……程度」,然后用「功……之」来修饰「程度」。致于是哪一方面的「功」,法师补充一个「于三宝」7。假若此分析无误,对「功课」二字的意思,兴慈法师的基本认知为「计算有多少功」,不过照一般语法习惯,这个的了解用「课功」来表达也许会比较顺些。8然而在兴慈原著出版后约八十年,人们大概不太会花时间来仔细解读、翻译其艰涩的文字,干脆把「儒」的「又谓」跟「释氏之言」混在一起,产生一个新的「因其冀获功德〔<以期成绩〕于念诵准则〔<准式〕之中」,甚且进而考虑到佛门形象,想避免道场住众被看成有企图、贪功德的,所以再次加工,形成更简化的陈述句「僧人在念诵时能够获得功德」。当然,这些无一不是缘起,不过笔者还是忍不住问:中国佛教「课诵」的「课」究竟含什么意思?于是拟藉《法光》杂志一角,不揣愚庸,简要考释,尚盼方家斧正为荷。从文献的历史考证获悉,「课诵」二字早在唐代的汉译佛典和本土著作里一并出现,甚至可发现一个比隋唐更早的例子,即南朝梁沙门僧旻、宝唱等集之《经律异相》。该书第十五卷《声闻无学第三.僧部第四》中收录《阿难奉佛敕受持经典供给左右》一则,故事后便用双行夹注的方式,先标示因缘的来源(「出《菩萨从兜率天下经》」),然后指出引文跟另一译本间的出入,说:「《贤愚经》云:阿难昔为长者,释迦为沙弥。师课诵经。乞食故,功程不上。长者愍之,仍给饮食。由是奉侍左右。」9由于夹注的文字极其扼要,于是进一步查「元魏凉州沙门慧觉等在高昌郡译」的《贤愚经.阿难总持品》来了解状况。该品以独立经文的格式呈现,说10:「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诸比丘,咸皆生疑:『贤者阿难本造何行,获此总持,闻佛所说,一言不失?』俱往佛所而白佛言:『贤者阿难本兴何福,而得如是无量总持?唯愿世尊当见开示!』佛告诸比丘:『谛听,着心!斯之总持,皆由福德。乃往过去阿僧祇劫,尔时有一比丘畜一沙弥,恒以严敕教令诵经11日日课程。其经足者,便以12欢喜;若其13不足,苦切责之。于是沙弥常怀14懊15恼:「诵经虽得,复无食具16。若行乞食,疾得食时17,诵经18便足19,乞食若迟,诵20则不充。若经不足,当21被切责。」心怀22愁闷,啼哭而行。时有长者见其啼哭,前呼问之23:『何以懊恼?』24沙弥答曰:『长者!当知我师严难,敕我诵经日日课限。若其足者,即以欢喜;若其不充,苦切见责。我行乞食,若疾得者,诵经即足;若乞迟得,诵便不充。若不得经,便被切责。以是事故,我用愁耳。』25于时长者即语沙弥:『从今已26往常诣我家!当供饮27食,令汝不忧,食已专心,勤加诵经28!』于29时沙弥闻是语已30,即得专心,勤加诵学31,课限不减,日日常度。师徒于是俱同32欢喜。33』佛告比丘34:『尔时师者,定光佛是;时沙弥者,今我身是;时大长者──供养食者──,今阿难是。乃由过去造35是行故,今得总持,无有忘失36。』尔时诸比丘闻是说已,欢喜信受,顶戴奉行。」这个本生故事里的师父严格规定他的沙弥弟子每天固定要背多少经文,也就是《贤愚经》所谓的「诵经……课程」或「诵经……课限」,沙弥到后来才因为那位仁慈的施主才能安心无虑地专心背诵而「课限不减,日日常度」。在此,「程」、「限」、「度」三个词,意思都一样,指「量」。37获得那么一种认知之后,再回到《经律异相》的夹注。现在就可以理解其中的「师课诵经」含「师父规定固定要背经」义,而「功程不上」指「所下的工夫达不到师父指定的量」。换句话说,南北朝唯一的「课诵」例其实不是一个词,因为第二个音节是跟后面的「经」构成一个概念(即「背诵经文」),而第一个音节的「课」是动词,意味着「叫(某人)固定作(某事)」。「课诵」这样不构成词的情况,持续到唐代。例如大唐西明寺沙门释道宣撰《续高僧传.习禅篇.唐雍州津梁寺释法喜传》所载:「荆州青溪山寺四十余僧。喜为沙弥,亲所供奉。昼则炊煮薪蒸,夜便诵习经典。山居无炬,燃柴取明。每夕自课诵通一纸。」38用法跟《经律异相》很像:法喜当沙弥时,白天忙着为僧众做事,晚上才可能拿起经典来读,而且遭遇没有现成的照明设备的困难,但法喜自我要求仍然强烈,自动自发每日夜晚固定背好篇幅一纸的经文。39另外在《读诵篇》,道宣收了《唐京师罗汉寺释宝相传》。其中提到宝相「六时礼悔四十余年,夜自笃课诵阿弥陀经七遍,念佛名六万遍,昼读藏经」40,用「笃」字来搭配,表示宝相每天夜晚非常认真41进行量由自己决定的固定修持。至于唐代的译本,有两个地方可以参考。一个见于唐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译《如意轮陀罗尼经.嘱累品》:「尔时观自在菩萨摩诃萨白佛42言:『世尊!我于无量劫来以大悲力受如来教,付嘱43有情,常随拥护,与其效44验。唯佛证知,为于有情说此如意轮陀罗尼明!若受持者依课诵持,得愿满足,证成不难。承佛神力,得作如是,救苦有情。』」45第二个翻译例原来是前者的同本异译,即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所翻《观世音菩萨秘密藏如意轮陀罗尼神咒经》。该经在《火唵陀罗尼药品》里说:「尔时观世音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于无量劫来以慈悲心受寄众生,常作拥46护,与其效验。佛自证知,为众生故。说此如意轮陀罗尼。若有受持、常自作课诵者,诸愿皆得。我承佛力,如是救苦众生。』」47前者的「课」、「诵」明显分开,「课」跟着「依」,而「诵」连结「持」,大体是说「依照固定的量念诵」,后者则逐渐迈向语词的凝聚,不过从译文的节奏来看,还是把「常自作课」看成前一译本「课」的扩充较好。这一点从另一同本异译获得进一步的证实,因为唐三藏法师义净译《佛说观自在菩萨如意心陀罗尼咒经》对等的文字说:「时观自在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于无量劫来以慈悲心于受苦众生常作拥护。惟48愿证知,为众生故,说此如意轮陀罗尼。若有受持、常自作业、专心诵者,所愿成办。我今承佛威力,如是救苦。』」49义净所谓「作业」对等于菩提流志的「课」及实叉难陀的「作课」。50「作业」可以翻梵语 krīya51,而 krīya 含「宗教仪式」、「祭祀」(或「供养」)等义52。印度传统宗教--这当然包括佛教53--仪式与供养往往不仅是要固定举行,而且量上(念诵多少次,供养几样物)也有规定。这在基本概念上跟华语的「课」颇为相同。至于赵宋的文献,无论是译典还是本土著作,「课诵」的例子明显增加。有趣的是,北宋翻译的经论,类别虽然多,但用到「课诵」的,正如唐代那两部同本异译,在《大正藏》里悉数归入《密教部》,包括西天中印度惹烂驮啰国密林寺三藏天息灾译的《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于波罗奈大城有一法师而常作意受持、课诵六字大明陀罗尼」)与《大方广菩萨藏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彼人随意受持作法者,食莲华根为斋,志心诵持真言三十六洛叉。课诵毕已,……」「坛法周足,勇猛精进,课诵相读,三昧不间」)以及宋契丹国师中天竺摩竭陀国三藏法师慈贤译《妙吉祥平等秘密最上观门大教王经》。后者的相关出处最多,诸如:「大善男子!若要成正觉,须诣菩提树,依过去诸佛秘密观门课诵修行。经一十二月,决成正觉!」「汝等若不依此秘密观门课诵修行,终不成于无上菩提!」「……每日寅午昏三时课诵供养。」「……各于本尊而申供养,课诵加持满一昼夜。」「五阿阇梨各念随方佛真言一万遍、菩萨真言一千遍,口诵真言,心专想佛、菩萨身光赫奕。既课诵已,阿阇梨等各随方坐,振铃课诵,献诸供养已,……」「与道场主忏悔发愿等及申供养不圆满事、课诵误错……」「五师各于随门广作种种法事供养,满一昼夜,三时课诵及烧护摩供养。」「凡欲课诵法事供养,先归命佛,念八大愿。」54无疑,当时移译的密续典籍中出现的「课诵」不再是松散的搭配,而是已凝成独立的词语。这个发展说不定跟着重行持仪轨的密续有直接的关系,甚至宋代的佛门史书里此因缘的影子似乎还看得到。参景定四明东湖沙门志盘所撰《佛祖统纪》,在《诸师列传.天竺式法师法嗣》下提及:「侍者思悟,钱唐人。侍慈云讲最久,故能深达观道。善持咒法,加水以愈人疾,求者如市。当课诵时,身及奉像,俱出舍利。」55当然,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正规密续的例子,不过持咒毕竟是密乘行者一个核心法门。总而言之,「课诵」固定成词的新用法逐渐普遍起来56,散见于不少学派的著作。天台的例子是宋天竺寺沙门遵式撰的《炽盛光道场念诵仪》在《第七行道方法》的标题下附双行夹注说:「行者当正身威仪,右绕法座,安庠徐步;称三宝名,课诵经典;了音声性空,亦知身心如云如影,举足下足,心无所得。亦知此身影现十方,充满法界,无不普现,围绕诸佛三宝……」57属于一般《法华》信仰的例子有宋宗晓编《法华经显应录》中《越州慧法师》「课诵《法华》,终身匪懈」和《明州誴大师》「课诵佛书,日有常度」。58偏重净土法门的可参《佛祖统纪.诸师列传.神照法师法嗣.樝庵有严法师》:「专事净业,以安养为故乡。作《怀净土诗》八章,辞情凄切,人多乐诵。常时所修三昧多获瑞应--施鬼神食,除病却崇,驱蛇去蚁;水旱禳禬,一为课诵,如谷答响。」59释文冲重校编集《慧日永明寺智觉禅师自行录》里第八十三则,则反映观音信仰:「普为一切法界众生昼夜六时别建道场,供养观音尊像,六时旋绕,课诵名号,愿诸众生五眼圆明,十身显现。」60特别是宋代组织规模庞大的禅宗,有例子规定「课诵」来培养一颗知恩的心,也有例子因考虑到场合的不当,所以禁止「课诵」。前者即比丘惟勉编次《丛林校定清规总要》第二卷所引《无量寿禅师〈日用小清规〉》:「如遇开浴,……出浴,……揖左右出,看设浴施主名字,随意课诵经咒回向。」61后者乃宗赜集《禅苑清规.出入》:「若有缘事全众出入,或赴斋,或念诵,或接尊宿,……三门下齐集。住持人行,次首座,次书状、藏主、知客、浴主、名德、勤旧,并依戒腊次第而行,直岁典座、维那、监院在大众后。庠序相随,无致差乱。不得左右顾眄,语言献笑,高声课诵,垂手掉臂。」62依这些释氏文献可确定,最迟在宋代,「课诵」已形成一个独立的语词63,而且都是当动词用,意即「固定念诵」。其中的「课」可以指时间、内容或者量方面的固定,是由名词演变成副词的,而原来的名词,在宋朝语言里仍然保留,诸如《法华经显应录.西京大圆禅师》「每夜持课」64或宋江西沙门晓莹集《罗湖野录》:「若也不能如是参详,不如看经持课度此残生。」65这样的组合是动词加当受词的名词。如果是时间副词跟动词的搭配,就有「日课」66一语,其后多接数目来表扬行持之勤,如《佛祖统纪》中「日课《莲经》一部」、「乃日课佛祖号千声,夜礼千拜,用为报恩」、「从其化者至有诵《弥陀经》十万至五十万卷者,念佛日课万声至十万声者」67、「日课佛名五万」、「日课佛至三万」、「日课千拜夜分乃寝」、「日课佛万声,二十年不辍」、「专心念佛,日课千拜」、「瑾日课利益二十事」68及宗晓编次《乐邦文类》第三卷《大宋永明智觉禅师传》「徒众常二千日课一百八事」69。部分例子仅提读诵的内容,而不特别点出数目,譬如《佛祖统纪》之「专志念佛,日课《观经》」、「日课《观经》,诵佛不辍」、、「日课《法华》、《楞严》、《圆觉》」和「日课佛号」。70此中「日课」原来可看成「日日课诵」的浓缩,接着则引申为「日日固定行持」,以礼拜或饶益众生的善业为对象。但语言的发展不会停顿的,所以最后「日课」还转变作名词用,如《佛祖统纪》中「常诵《弥陀经》为日课」71或者最特别的例子──因为是带点讽刺的味道──,即径山能仁禅院住持嗣法慧日禅师蕴闻上进《大慧普觉禅师语录》第十九卷《示清净居士》所谓:「有一种人早晨看经、念佛、忏悔,晚间纵口业,骂詈人,次日依前礼佛、忏悔,卒岁穷年,以为日课。此乃愚之甚也。」72由以上初步考查应该可以肯定:当今佛门常用的「早课」、「晚课」、「早晚课」或名词「课诵」,都是在上述语言历史的基础上衍生的。其中「课」的成分显然跟「计程度」、「图功德」或「有老师上课」的「课」不相干,而单纯着重于该修持行为在时间、内容或量上颇为固定。1 见《汉语大词典》11.281 a。2 同上,11.282 b。3 「进行教学活动,传授知识」下列出两个书证,即清昭槤《啸亭续录·张夫子》「公独处萧寺中,聚徒课读」和徐自华《九日闲兴》诗「懒携樽酒登高去,课读儿曹昼掩扉」,「接受教育,学习知识」则单引《儿女英雄传》第十八回:「纪太傅听说无法,便留纪望唐一人课读,打算给纪献唐另请一位先生,叫他兄弟两个各从一师受业。」4 见 ,15.1.2011。5 见 ,16.1.2011。6 见 Marcus Günzel, Die Morgen-und Abendliturgieder chinesischen Buddhisten 第 209页 (G ttingen: Seminar für Indologie undBuddhismuskunde, 1994)。新式标点符号为笔者所加。7 Günzel 上引书第 21 页将「然我释氏之言功课者,谓计功于三宝之程度以为日用之准式也」句德译成 “Was wir, die Angeh rigen ākyas, als ‘Unterricht’ bezeichnen, bedeutet,das Berechnen der [eigenen] Verdienste nachdem Standard der drei Juwelen als t glicheRichtschnur zu nehmen”,把这个语法关系弄错,竟以「功」为「计」的对象而用「三宝」来修饰「程度」。再加上对个别语词的误解,诸如把「功」看作「功德」(“Verdienste”),将「程度」说成「标准」(“Standard”),视「我释氏」为「我们──释迦的亲人──」,且以「功课」为有老师在上课的「课」(“Unterricht”)等等,使得译文跟原文之间的落差有如天壤之别。8 据《汉语大词典》11.277 b-278 a,「课功」含有「考核功绩」、「监督做工」二义(最早的书证为宋王安石诗),跟佛门所谓「功课」了无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卷子里发现的唐五台山竹林寺法照法师的《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载有《极乐宝池赞》和《净土五字赞》,而这两个赞都用到「课功」。前者说「众生念佛莫狐疑 决定西方七宝池 每月课功千万遍 回愿弥陀早已知」、「课功作意由人进 念佛多者紫金台念佛之人求愿往 直至西方七宝池」,后者则说「净剎西方好 人人道可怜 课功勤念佛 永得离人天」(分别见 T 85.2827.1260a 3-4、18-19、1265 a 18-19)。由语境来判断,这边的「课功」大概指「固定持名念佛次数的成绩」。9 见 T 53.2121.79 c 9-10。据《大正藏》斠勘记(以下版本出入也都参考该藏斠勘资料),「乞食」前,《高丽》、《大正》二本有「为」字,兹从《旧宋》、《宋》、《元》、《明》四藏;「不上」,兹从《旧宋》本,他本作「不止」;「饮」,《高丽》、《大正》二本作「衣」;「右」后,《高丽》、《大正》二本有「也」字。10 见 T 4.202.417 a 12-b 9。唐译经证义讲经律论广演大师遇荣集《〈仁王经疏〉法衡钞》援引《贤愚经》此段,见 X 26.519.446b 22-c 8。11 「教令诵经」四字,唐译经证义讲经律论广演大师遇荣集《〈仁王经疏〉法衡钞》引文作「而令读经」,见 X 26.519.446 b23-24。《〈仁王经疏〉法衡钞》把此故事中所有「诵」字都改成「读」。12 「便以」,《〈仁王经疏〉法衡钞》作「师便」,见 X 26.519.446 b 24。13 「若其」,《〈仁王经疏〉法衡钞》作「若经」,见同上。14 「常怀」,《〈仁王经疏〉法衡钞》作「情怀」,见同上 446 c 1。15 「懊」,《宋》、《元》、《明》三藏作 「忧」。16 「复无食具」,《宋》、《元》、《明》三藏作「食复不周」。17 「诵经虽得,复无食具;若行乞食,疾得食时」,《〈仁王经疏〉法衡钞》略引为「若疾得食」,见同上。18 「诵经」,《〈仁王经疏〉法衡钞》改为「读经」,见同上。19 《〈仁王经疏〉法衡钞》在此多出「师徒欢喜」句,见同上 446 c 1-2。20 「诵」,《〈仁王经疏〉法衡钞》作「读」,见同上 446 c 2。21 「若经不足当」,《〈仁王经疏〉法衡钞》作「便」,见同上。22 「心怀」,《〈仁王经疏〉法衡钞》作「沙弥」,见同上。23 「之」,《高丽》、《大正》二本作「言」。24 「见其啼哭前呼问之何以懊恼」十二字,《〈仁王经疏〉法衡钞》略引为「见而问之」,见同上 446 c 3。25「 沙弥答曰……我用愁耳」七十二字,《〈仁王经疏〉法衡钞》浓缩成「沙弥具答」,见同上。26 「已」,《高丽》、《大正》二本作「以」。27 「饮」,《宋》、《元》、《明》三藏作「养」。28 「食已专心勤加诵经」八字,《〈仁王经疏〉法衡钞》作「食已读经」,并附「我愿当来多闻总持」句。29 「于」,《宋》、《元》、《明》三藏及《〈仁王经疏〉法衡钞》作「尔」。30 「闻是语已」四字,《〈仁王经疏〉法衡钞》无。31 「即得专心勤加诵学」,《〈仁王经疏〉法衡钞》作「即得读学」。32 「同」,《宋》、《元》、《明》三藏作「用」。33 「师徒于是俱同欢喜」八字,《〈仁王经疏〉法衡钞》作「师徒欢喜」。34 「比丘」前,《〈仁王经疏〉法衡钞》有「诸」字。35 「造」,《〈仁王经疏〉法衡钞》作「修」。36 「今得总持无有忘失」,《〈仁王经疏〉法衡钞》作「今得无量总持」。37 参《广雅.释诂》三:「程,量也。」(见徐复主编《〈广雅〉诂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第 271 页。)《原本〈玉篇〉残卷》引王逸《楚辞》注:「限,度也。」(顾野王《原本〈玉篇〉残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第 490 页。)《左传.文公十八年》「事以度功」杜预注「度,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