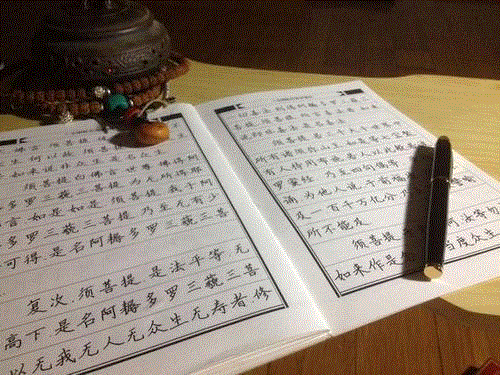他不是文艺青年想像中的李叔同,他是弘一法师
发布时间:2023-09-18 01:32:25作者:药师经全文弘一法师圆寂的晚晴室,位于泉州第三医院(精神病医院)的院内。从模范巷的小门入,可见一条长长的石板路,两旁的石砌墙体灰暗而压抑。医院已经迁址他处,人去楼空,一片萧瑟的气氛。
绕过废弃的病院大楼,便可见一座孤零零的牌坊,那是南宋所立的小山丛竹书院遗址,也是不二祠的旧址,与韩愈同榜高中的欧阳詹曾在此读书,后人为纪念这位高中进士的泉州乡贤,特立不二祠。朱熹在任泉州同安主簿时,因仰慕欧阳詹之风而常来此地讲学。
如今这个小小的院落里,只剩下了三间晚晴室。
晚晴室堪称近代佛教史上“最文艺的人生告别之地”。弘一大师不仅临终前在此地写下著名的“悲欣交集”,引得一片感叹与臆度,而且在提早准备好的遗书里,还留下了后来被广为传诵的诗偈——“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无论是“悲欣交集”,还是“天心月圆”,在后世的口耳相传中,渐成一种文艺的想象,全然无视里面的佛法意涵。但是,正如昔日曾有人问弘一大师,来访大师求字的的人如此之多,但全无一人来问法者,真是令人遗憾。弘一法师却回道:“我的字即是法”。或许,通过弘一大师所遗留下来的片言只语,能让人与佛法结上一份看似不经意的因缘,正是他的良苦用心吧。
靠近细看,晚晴室的三间房屋已经人去室空,其中两间门锁紧闭,另外一间开启的房间也无任何家具,墙上贴着未处理掉的精神病院工作章程,显示这里曾是作为医院办公场所之用。
我用手机搜索出弘一大师圆寂时的相片,透过窗户比对着室内的空间格局与细节,虽然地砖的样式似乎并未改变,但仍没有找到足够确凿的标志物。经过反复地观察,我大概推断出当年弘一法师圆寂可能所处的房间。
对着房间合十,遥想昔日弘一法师每日在此静省念佛的情景,对比今日晚晴室的无常朽败,心中升起一股莫名的感触。
晚晴室前,一株不知名的大树,树叶繁茂,旁有石板,可供闲坐。东南外海已有台风预报,不时有夏日凉风吹过。晚晴室是这次福建参访的最后一站,恰好也是弘一大师圆寂之地,多少有一些冥冥暗示的意味。
弘一法师圆寂处——晚晴室坐在树下看着静谧的晚晴室,似乎并无多少可看之处,但却又觉得此处有无尽的宝藏等待去发掘。终了,起身欲离开,有丝丝小雨落下,天也渐感微凉。
这次来访福建,本来是要去探访明清之际的黄檗僧——隐元隆琦的行迹。年初的九州之行,我在长崎参访了隐元隆琦从福建渡海来日驻锡过的几座寺庙,对这段明清之际的中日禅宗交通史顿时有了相当的兴趣。隐元隆琦从法脉上直承清初天童名僧密云圆悟,本属临济一系,但却在日本开创了和临济、曹洞并列的黄檗宗,可谓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虽然还没有机会去造访位于京都附近的黄檗宗大本山——万福寺,但我回国后却一直有心要去参访隐元隆琦位于福建福清的道场——黄檗山万福寺。
但这次的福建之行,本来是一次寻找隐元隆琦的旅程,却无意中被弘一大师的因缘带向了另外的方向。
因为行程的关系,在造访雪峰崇圣寺与鼓山涌泉寺之后,我们径直赶往厦门,与多年未见的大学老友会面。这是我第一次来厦门,见到老友,在夜晚的海滩边遥望渔火点点的金门岛,心情很兴奋。
入住与鼓浪屿对岸而望的宾馆,突然生起一念,想上岛看看。于是在夜间搭乘游轮前往鼓浪屿,沿着环岛路四处闲看,突然见有日光岩寺,突然想起弘一大师曾于此闭关静修,遂入寺礼拜。
日光岩寺规模不大,有佛殿若干,数位比丘尼于夜色中念佛经行,正面石岩中供有佛像,偶有香客前来祈福。拾步登上一旁石阶,可见石墙上镌刻有“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八字偈颂,绕过石墙,见弘一大师石像。
厦门鼓浪屿日光岩寺中的弘一大师像1936年5月,重病初愈的弘一大师来到日光岩闭关静修,但也未得清闲,不仅关中处理各种来信与编辑事务,而且还要接待各路访客,其中就有著名的郁达夫,尽管弘一法师对这位年轻作家的背景所知不多,也多以郁居士相称。而在郁达夫回忆这此见面的诗中,他也多少透露出一些“逃禅”的想法:“中年亦具逃禅意,莫道何周割未能。”
不过,让弘一大师离开日光岩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寺中每日锅碗瓢盆声与厨娘的大呼小叫,令人不胜其扰。于是在此地居住半年之后,弘一大师前往南普陀,为众讲解《随机羯摩》等戒学内容。但他也并未能安住南普陀,在给胜进居士的信中,他如此袒露心迹:
“迩来心绪不佳,诸事繁忙,养正院训育课,拟请仁者代授。四月初旬,讲律事即可结束。将往他方,埋名遯世,以终其天年,实不能久堕此名闻利养窟中,以辜负出家之本志也。”
弘一大师有离开南普陀的想法,除了信中所描述的理由之外,实有对当时闽南佛学院学僧状态之失望。在1937年初,他在养正院讲述《南闽十年之梦影》,对这十余年来在福建的行迹作一番自己的总结,演讲中他反复强调佛教徒要重因果报应,不能让俗人轻视,尤其对出家人的角色有不少可称为言重的警醒。
厦门植物园内,有小寺数座,多与弘一大师有缘。穿过各种不知名的植被与树林,渐见狮山的摩崖石刻,石径旁分一路,举目可见两座并排的山门,一题“万石莲寺”,一为“中岩寺”。“万石莲寺”即“万石岩寺”,时任南普陀的主持会泉法师邀请弘一法师在中岩闭关,但关房尚未建设完毕,于是从1937年3月起,弘一大师暂居万石岩寺。
厦门狮山万石莲寺与中岩寺正在寺前的摩崖石刻前徘徊,身旁一位比丘尼黄衣翩翩,匆匆入寺。紧随其后,可见一牌坊,上书楹联正是弘一法师为万石岩寺所题——“一句弥陀声传鹭岛,千年常住业绍庐山”。短短两句,可见寺庙专修净土法门的旨趣。山寺紧靠巨岩,布局紧凑。绕殿一周,民国海军上将萨镇冰等人的题词赫然可见——“经翻贝叶云生榻,定入蒲团月绕檐。”
万石莲寺弘一题联出寺门,折向相邻的中岩寺,与万石岩相比,中岩幽深僻静,更适合闭关静修,难怪弘一大师有意在此长住。入寺,一段山路后,抬头可见门扉大开,上书“放开眼界”,入内,可见小殿,供有菩萨像,旁有一路通往岩顶。在此静修,当可避免游人惊扰。
但弘一大师的闭关心愿仍未实现,不久,他就接受倓虚法师的邀请,北上青岛湛山佛学院讲学。之后回到闽南,仍然四处暂住,虽能短期闭关,但从未实现昔日五年掩关的愿望。
这或许是弘一大师以文人名士身份出家而不得已面对的因缘吧。
1918年8月19日,弘一大师正式于虎跑寺剃度,然后前往灵隐寺受戒。因为李叔同的名士身份,所以方丈和尚对他礼遇有加,安排住在客堂后的芸香阁里,而非条件艰苦的戒堂里。但戒场的开堂和尚慧明法师对他说:“为什么不进戒堂呢?虽然你是读书人,但读书人就可这样随便吗?就是皇帝,我也一样看待。”
受戒前后,过去曾在佛学方面给予弘一很多帮助的马一浮,也特地送来《灵峰毘尼事义集要》与《宝华传戒正范》,皆是戒学典籍。弘一读时非常感动,也就在此时,他发愿要学戒弘戒,正式确定了出家之后的方向。
受戒之后,按照一般出家人的选择,大抵是要在大丛林里安住参学的,学习传统丛林的规矩。可是如果仔细观察弘一大师出家后所居之地,我们可以清楚地发觉,他四处游走,主要目的是想觅一处地方闭关学戒。
受戒之后,他留在杭州玉泉寺短期居住,又去虎跑大慈寺结夏安居。次年在浙江富阳新登贝山闭关数月,出关后则前往衢州,住莲花寺。
在此后数年里,弘一大师基本在杭州玉泉寺、温州庆福寺、衢州莲华寺、三藏寺、杭州招贤寺等地居住,如果细考这几处的特点,要么是幽静山林,要么就是偏地古寺。弘一大师四处游走的真实想法,就是寻找一处可以长久闭关之所,来研习戒律。在贝山居住期间,他曾自述:
“庚申之夏,居新城贝山,假得《弘教律藏》三帙,并求南山《戒疏》、《羯磨疏》、《行事钞》及灵芝三记。将掩室山中,潜心穷研律学;及以障缘,未遂其愿。”
事实上,在这样动荡的环境下,他仍然完成了一些重要的工作,如在衢州期间,弘一大师基本完成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并校对了《菩萨戒本》。如此烦累的工作和不安的环境,也让他身心颇有不能堪负的问题,因而印光大师得知之后也来信告诫,不宜研习教典和写经,而应专心念佛。
不过弘一似乎并没有听取印光大师的告诫,在接下来数年里,他不仅书写了大量佛经,而且断断续续地闭关,抄写佛经和研习《四分律》。在他写给刘质平的信中,他曾表示会在温州庆福寺闭关五年,但不到两年,他就离开温州,前往沪杭等地,后又陆续在衢州、温州等地停留,虽有短期掩关,抄经研律,但均未实现他长久闭关的心愿,也很难实现他在写给印光大师信中所誓欲证取的念佛三昧境界。
时局动荡,也是他无法安心闭关的重要原因。1927年,弘一大师本在杭州云居山常寂光寺闭关,但北伐军起,革命思潮澎湃,当地也颇有青年人兴起灭佛舆论,弘一大师写信给相识的堵申甫居士,表示次日出关,好护持佛教。出关后,弘一大师召集当地较为激进的青年政治人物来寺会谈,先手写劝诫纸条若干,分赠诸位到会者,其中最为激烈的一位青年,出寺后感叹道,今日天气寒冷,为何有浃背之汗?杭州灭佛舆论不久就告熄灭。
弘一大师背后所站立的“李叔同”,是他永远驱除不了的影子。世间人看弘一,其实只不过是在看一个“无法理解”的李叔同而已,他们心中的弘一,还是演茶花女的李叔同,是在东京美术学校一鸣惊人的李息霜。
2015年春节前夕,我在东京旅行,参观完国立博物馆,就在附近的上野公园闲逛,不经意间走入一条幽静的道路,似像是学校,再走一段,看到了牌匾——东京艺术大学。当时心中并不知道这所学校有何重要,只是觉得或许可以看看日本的艺术大学有什么样的特色。时值假日,校园几乎不见学生,除开偶尔遇到的不熟悉的铜像外,还有音乐系所立的贝多芬塑像。当时只是感觉,这所大学,小而雅致。
东京艺术大学后来仔细阅读读李叔同的传记时,见文中常提及他在日本留学时所居住的地方就在上野公园附近,而东京美术学校就在上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李叔同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在这里,他认识了那位后来被世人尽情演绎的日籍妻子,也就在这里,他得以两次参加了美术学校最高级别的白马会展览,名声大噪。而也正是在这里的学习经历,将他推向了西湖边的杭州第一师范学校,认识了夏丏尊与马一浮,走向了虎跑,最终促成了他的出家因缘。
不过,现实环境一再的变动,让弘一大师出家之后长期闭关的愿望始终难以达成,他的学生刘质平、丰子恺以及老友夏丏尊动议在白马湖边为他建造一座闭关房,取名“晚晴山房”。但就在同年,弘一大师在上海造访恰好路经此地的友人尤惜阴居士,听说他们要前往暹罗弘法,弘一大师当下决定要与之同去,次日就于十六铺码头动身出发。
如此看上去似乎略显草率的决定,是否是因为弘一对于这十年来在江浙各地的奔波渐已厌倦,或许很难仓促定论,但是可确定的是,弘一大师内心中想要闭关静修的想法不仅没有消磨殆尽,反而越来越强烈,大概是他能如此决断下南洋的重要诱因。正因此,也让弘一大师与闽南结下最后十余年的深厚因缘。
因为身体原因,弘一大师并未前往暹罗,而是在厦门逗留了四、五个月,闽南的气候让他感觉非常舒适,在给刘质平的信中,他写道:“南闽冬暖夏凉,颇适老病之躯,故未能返浙也。”就在此年,他第一次前往南安小雪峰寺度岁。
次年回到江浙,但似乎对在白马湖边闭关失去兴趣,而是请夏丏尊等人改而迎请虎跑寺的弘祥法师来此居住,自己则表示要去福建长住。就在1929年10月,他第二次回到厦门南普陀,而在年底,他再度前往南安小雪峰寺度岁,也就在这里开启了近代佛教史上的一段佳话。
南安杨梅山,是唐代著名禅师雪峰义存的出生地,后来雪峰义存在闽侯雪峰开山,大倡禅风,后曾回南安为父母守灵。有僧人因仰慕雪峰义存之德行,于是在杨梅山建寺,同样取名“雪峰”,但为与崇圣寺相区隔,一般被誉为“小雪峰寺”。
从泉州前往小雪峰,并无任何公共交通,只能包车前往,司机一路感叹,这种地方从未载过游客来此地,他也是头次来云云。但是他补上一句,曾载过一位专门研究佛教的学者去过弘一大师曾驻留过的晋江草庵寺,那也是中国唯一尚存的摩尼教寺庙。
小雪峰从建筑来看,并无太多可谈之处,大抵属于闽南寺庙一带的风格,许多皆为新建,径直上高处,见一殿,名为“华严宝殿”,内有几位居士,一位妙龄女子跪于普贤像前诵经,轻声问其中一位,晚晴亭和太虚洞在何处?她指着殿后方:“喏”。
绕至殿后,一座孤亭伫立潭边,“晚晴亭”三字为赵朴初所题,亭中立有一碑,载有立亭之因缘。
南安小雪峰寺晚晴亭1929年岁末,弘一前往小雪峰度岁,时在南普陀讲学的太虚大师也与芝峰法师同往,在雪峰相遇。太虚作为现代革新佛教的代表人物,与谨守佛律的传统派代表弘一法师并无半点牴牾,据说还曾在太虚洞整日论说佛法,彼此唱和。
太虚大师因钦慕弘一大师德行,特地题偈赞叹——“圣教演心,佛律严身。内外清净,菩提之因。”如今,太虚大师亲题的赞语已镌刻在晚晴亭两侧石柱之上。住持转逢和尚得见两位高僧在小雪峰共聚度岁,于是分建晚晴亭与太虚洞,纪念这段近代佛教史上的因缘。
几位本地的年轻人在亭边徘徊,不过他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一汪潭水。在碑前合十礼拜后,我转而想寻觅太虚洞,可是绕至后山,经过转逢和尚塔,前面便是一片杂树林,寻路几不可得,遂折返至大殿,咨询寺内居士,告知就是那条路线继续前行,于是再度鼓起勇气上山寻觅,山路越发难行,路边多有巨石,但不见半点太虚洞之踪迹。体力殆尽,遂只能接受当下因缘,折返休息,心中暗叹一句:“真是晚晴易觅,太虚难寻啊!”
小雪峰地理偏远,寺庙经济想必并不宽裕,寺内建设也有延宕的迹象,各种法会讯息也透露出,所有的经济收入似乎只能靠法会来支撑。但无论如何,这里毕竟是雪峰义存的出生之地,也有太虚与弘一这样的僧人前来相会,佛法讲一切皆有因缘,或许,如此偏远的山寺就是依此因缘闪烁出佛种延续的光芒吧。
弘一法师在小雪峰度完年后,回到泉州承天寺。承天寺乃闽南名刹,寺内照壁就有“闽南甲刹”的赞语。山门并不起眼,上悬“月台”二字,入内只见宽而悠长的石板路,两侧皆为白墙,右侧墙上则有弘一法师所题《华严经》句,异常醒目。
路边有一小门,上书“月台别院”,入内才知这是弘一大师昔日在承天寺所居之处。1930年初,他应性愿法师邀请来此为月台佛学研究所上课,每日除上课之外,就为各方求字者题字,他也为优秀学僧题字,常写的就是“以戒为师”。
承天寺月台别院中的弘一大师像现在的“别院”已非当年旧物,而是依据当年的格局重建而成,以作纪念。内有僧俗各一,与我谈起弘一大师昔日在此日的光景,那位居士不停地感叹:“现在没人学了,没人学了啊。”
可是,就算昔日弘一大师尚在之时,又有多少人愿意跟随学习呢?
离开承天寺后,弘一大师回到浙江,在温州时因患痢疾而养病数月,后辗转至慈溪金仙寺和五磊寺,本欲建立“南山律学院”培养僧才,但也因与主事者无法投契而离开。此次讲律未果的事情,对于弘一大师深有打击,“我从出家以来,对于佛教想来没有做过什么事情。这回使我能有弘律的因缘,心头委实是很欢喜的。不料第一次便受了这样的打击。一月未睡,精神上受了很大的不安,看经念佛,都是不能。”
在浙江逗留的这一年多,弘一大师常常患病,曾在上虞的法界寺染上伤寒,甚至开始和夏丏尊与主持法师商议料理后事的问题。就在1932年10月,他再度回到厦门,就在万石岩寺不远处的万寿岩寺安居。
在这段时间,弘一大师主要在厦门与泉州之间往返,他长居闽南的心情也越发强烈。他在这段时间梦见身为少年,与儒士同行,听见有人诵读《华严经》,并见十余位长髯老人围坐论法。弘一大师认为,这是他余生在闽南弘法的梦兆。于是他开始积极地讲说戒律学,并编写各种教材,鼓励听众发愿学律,其中颇值一提的就是在泉州开元寺为学僧讲律的因缘。
在今天如果乘坐出租车是无法直接抵达泉州开元寺大门的,而是只能步行慢慢沿着西街靠近,不久可见远处立有一塔,气势雄浑,顿有时间倒流之感。开元寺山门与天王殿合二为一,殿顶狭长,“紫云”之匾远看则藏于屋檐之下,靠近则可得见全貌。
泉州开元寺开元寺内景一入殿内,顿有敞亮之感,朱漆开元寺匾额之下,两侧所挂即是弘一大师所书楹联,那是朱熹昔日赞叹泉州之语——“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
1933年,弘一大师带领十余位欲学戒律的学僧从厦门来到开元寺,在尊胜院内讲《南山钞记》,并带领大家一起圈点,并不时出考题检验学僧学习情况。
尊胜院今日已经改为弘一法师纪念馆。馆前有一庭院,中树弘一汉白玉半身像,绕过塑像,可见纪念馆照壁上刻有“悲欣交集”四字,馆内展有弘一法师生平行迹。
开元寺内弘一法师纪念馆在泉州停留期间,他也常去承天寺为学僧讲学。这段时间,弘一法师虽然往来于厦门、泉州,但是其讲学与校勘律学典籍的进度明显加快。而在晋江草庵寺居住期间,他开始阅读见月律师的《一梦漫言》,在跋文中,他谈到读到此书时的感触:“欢喜踊跃,叹为希有。反复环读,殆忘寝食。悲欣交集,涕泪不已。”
这番感动,或许是弘一法师与见月律师见律学不彰的悲痛共鸣,但也更让他产生“誓愿尽未来际,捨诸身命,竭其心力,广为弘传”的愿望。
在开元寺内一个博物馆内,我看到一幅弘一法师所写的条幅,看题款,是弘一在1938年承天寺佛七圆满时所写,内容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如果考虑到此时福建所面临的抗战氛围,当能明白弘一大师对于时局的关切。
就在1938、39年间,弘一法师四处弘法的速度似乎开始成倍增加,无论是泉州、厦门,还是漳州、惠安和安海,他拖着衰病之躯四处讲《普贤行愿品》、《心经》、《地藏经》等,并且不停地将手书的华严经偈赠给有缘之人。在他写给丰子恺的信中,他提到预感不久于世,因此只能勉力弘法,报答闽南信众之恩。
越深入地探访弘一法师的行迹,我越感觉无法跟上他的步伐。如果说他刚来闽南时的节奏是缓慢而随缘的,并且一方面急切地想要寻找静修闭关之所。但到了后期,他的行走越发地疾速,也很少提长期闭关的事情;另一方面,抗战交通的不便,也使得他的弘化路线变得更加复杂,而他几乎在任何一家所驻留过的寺庙都在尽力的讲学与不停地赠字,同时还不忘对过去没有完成的一些典籍校勘作最后的补注。
在泉州的百源路上随意游走,路边见一小寺,抬头一看大殿牌匾——“铜佛古寺”,啊,又是弘一法师的题字。这座城市似乎与弘一法师融为了一体,你很难不会注意到这位律学僧人给这里留下的细无声的温润影响力。古寺旁,一间相当洋气的露天咖啡馆紧靠百源清池边,点好咖啡,闲坐在庭院中的参天古树下,头脑中的时空感似乎有一点失重与错位。
我无意中卷入到一场寻找弘一法师的参访行程中,却在这段旅途中,被慢慢带入一场时空加速的漩涡之中。当我停下脚步,不再一座座地细数弘一法师所曾驻锡讲法的寺庙,而只是在这座小小的咖啡馆感受闽南一地与弘一法师的关系时。我突然意识到,其实并不需要跟随他去做那么多的长途跋涉,你所走过的每一寸闽南的土地,那位衰病的僧人都已率先踏足而上。
可是,我仍然无法摆脱寻找的执着感。
次日,我们登上清源山,寻找到弘一法师的舍利塔。游客寥寥,扫塔供养,绕至塔后诵读一卷《普贤行愿品》,这是弘一法师用力最深的一部佛经,在他看来,这是《华严经》的精华所在,而他毕生所依的经典,正是《华严经》。
泉州清源山弘一大师舍利塔塔内除弘一法师的舍利塔外,塔后的碑上所刻,是他最亲密的弟子丰子恺所画的大师像。丰子恺所画的同一风格的画像,在南普陀五老峰上的太虚大师纪念碑上也可见到,在太虚纪念碑上,刻着弘一法师所书的华严经偈——“当令众生喜,能报大师恩。”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弘一法师对太虚大师昔日在小雪峰偈赞的最后回应吧。
在弘一大师像两侧,镌刻的是他在开元寺为“南山律苑”所题的自勉语——“愿尽未来,普代法界一切众生,备受大苦;誓捨身命,弘护南山四分律教,久住神州”。如果不能理解这两句话的内涵,大概就无法真正体解那位在西湖边出家的李叔同的真实内心与追求,而只能陷入到无止境的猜疑与惋惜之中。
俗情与圣意,大抵是宗教所区分的界限。不过佛法中本无“圣凡”的绝对对立,故有禅宗涤荡一切执着束缚的潇洒与自在。

1942年初,弘一法师在温陵养老院静修闭关,关中所写的书信似乎透露出不久于世的讯息。在七月间,他在晚晴室旁的庭院里为几位法师演示剃度仪式,并撰写《剃发仪式》一卷,交付于人,嘱托未来可依此仪轨进行如法的剃度。八月,弘一法师的身体更加衰弱,他一方面写信给相识之人交代后事,一方面也叮嘱侍从的妙莲法师相关助念和毘荼的事宜。
泉州承天寺九月初四日,弘一法师以吉祥卧姿,留下那一幅令人动容的涅槃相,最终告别人世。两日后,灵龛送往承天寺化身窑进行毘荼。
在承天寺里,当年的化身窑早已不存,只留下一块石碑标记着昔日弘一大师的人生终点。他的舍利后来分为二份,一份入清源山舍利塔,一份则由昔日在厦门大学认识的刘梅生居士送回杭州虎跑寺供奉。
承天寺弘一法师化身处到了这里,作为历史记忆的弘一法师,我的寻找之旅似乎可以圆满结束了。不过,弘一法师的影响似乎并没有消失。
1936年,一位名为圆拙的年轻僧人进入闽南佛学院就学,恰逢弘一法师此时在佛教养正院讲学,得以相识。1937年,圆拙法师跟随弘一法师北上青岛湛山佛学院,随从学律,虽只有短短的半年时间,却让他终生受益。
1982年,正值佛教界万废待兴之时,时任广化寺的主持圆拙法师特别遴选五位年轻僧人专心学习律学,时间长达五、六年之久。这五位僧人,后被教界称为当代的“南山五比丘”。
其中的界诠法师最终建立了汉传佛教最大的律学道场——福鼎平兴寺;济群法师则在全国掀起一股居士佛法教育的浪潮;还有隐于闽南佛学院默默进行僧教育的演莲法师。而今天在著名的北京龙泉寺致力于让佛教与现代社会转型接轨的学诚法师,也是圆拙法师培养出来的僧才之一。
2017年10月13日,是弘一法师圆寂75周年的纪念日。那位喜好孤身独处,寡于交游的弘一律师,竟以这样的方式给汉传佛教留下了如此重要的遗产。
原来,这才是佛法中的“渊默雷声”。
【注】本文原标题《寻找弘一》,配图均为作者提供。
【责任编辑:贾嘉】 sh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