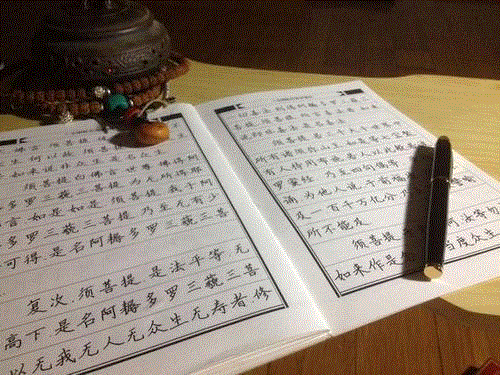300年的寺院 30年的学院——有感于参观西黄寺给人的视觉和心灵双重冲击
发布时间:2023-08-11 01:31:31作者:药师经全文新年伊始,隆冬腊月,一个晴好无风的日子里,前往西黄寺参观游览。从北三环中路的安华桥西下车,抬头向南望去,不远处一座黄琉璃瓦覆盖的殿宇顶端在灰色水泥砖墙的现代化楼群中赫然入目,令人神往。
一踏进这座闹中取静的肃穆寺院,顿时将刚才的车水马龙、世俗喧嚣抛在高墙之外,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另一番天地。不由得心中感慨,真是大隐隐于市啊!走在青砖相衔的古甬道上,映入眼帘的是宽豁院落,红墙绿瓦,苍松翠柏,殿宇堂皇,石塔嵯峨,牌楼恢宏,布局严谨,气势非凡……300多年积淀的岁月沧桑感扑面而来。恍惚间物我两忘,似乎晨钟暮鼓在耳边响起,清风明月揽入怀中。沉浸在此种凡间稀有的佛界圣境,万虑消停,心静无思,怎能不令人陶醉呢?
值得一提的是,此行由统战部有关领导联系促成,得到院方的充分重视和周密安排。尤其是派一位看上去年纪轻轻却佛学造诣深厚、相当于博士的一级经师担任导游,为此行20余人进行了声情并茂、如数家珍的全程讲解。大家一路上紧随导游,边走边看边听,不仅对西黄寺进行了全方位的观察,而且对以往感到新奇陌生的藏传佛教历史有了较为明确的认知,解开了心中困惑已久的一个个谜团。

西黄寺的来历是什么?为什么西黄寺建成300多年没对外开放过,绝大多数北京人都无缘一睹真颜呢?说来话长,当西藏还是一片荒蛮之地和一群部落,只知道膜拜原始图腾的时候,藏王松赞干布依仗父辈奠定的雄厚经济基础,征讨叛乱部属归其治下,统一了西藏各部落,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历史上处于上升时期的统治集团无一例外地具有创新思维,有着与外民族进行文化交流的强烈欲望。松赞干布正是在吐蕃初建时政绩宏伟、风俗纯良的条件下,颇具远见卓识地委派吞尼桑不扎等人出使佛教发源地泥婆罗国(尼泊尔旧译)和崇信佛教的唐朝。除了请婚通好,还派人学习印度和汉地佛教文化,创制了现在所使用的藏文,翻译佛教经典。译经的出现,使松赞干布开创发展的佛教在吐蕃顺利传播开来,在信仰、法律、道德和生活习俗上对人们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从上层到百姓无一不是虔诚的佛教徒。从此,西藏渐渐演变成政教合一的体制,宗教领袖也就是地方首长。虽然内地的改朝换代和西藏并不同步进行,但西藏一直都是和内地紧密相连的。话说明朝永乐七年(1409年),藏传佛教格鲁派创立者、出身佛教家庭、通达显密各派教义的宗喀巴大师于拉萨大昭寺发起大祈愿法会,被公认为西藏佛教界的领袖,格鲁派成为西藏第一大教派,藏传佛教信徒大多崇奉宗喀巴为教主。为振兴戒律,宗喀巴戴上了与过去持律者们同样的黄色帽子,以后弟子们也随着佩戴黄色桃型僧帽,所以又叫黄教。宗喀巴的徒弟在他去世后传承其教义,三徒弟成了一世班禅,最小的八徒弟就是一世达赖。到明末时期,西藏其他地方政权和派系的威胁使格鲁派慢慢衰落。于是格鲁派借助强大的漠西蒙古准噶尔汗国的固始汗王打败了他的敌人,稳固了在西藏的宗教中心地位。这时,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为了和内地加强联系,便一起委托青海宏善寺的六世巴周活佛色钦曲杰金巴嘉措赴东北联络后金。金巴嘉措到了古沈阳皇太极的盛京,很快就和皇太极合谋一处,皇太极利用格鲁派宗教的影响,兵不血刃地把蒙古纳入版图。皇太极给金巴嘉措在盛京城外建了四座尊胜佛塔和寺,就是沈阳老城外的东西南北塔,都是藏式白塔。清廷进京,顺治登基后,金巴嘉措提议在北京建塔,“欲以佛教阴赞皇猷,请立塔寺,寿国佑民”。当时北京已经有了白塔寺,但那是元朝盖的,不灵了。于是,这时已经开始亲政的顺治就同意金巴嘉措在距离紫禁城最近的北海琼华岛上建了一座永安寺白塔。就像高香要烧三柱一样,金巴嘉措在城北仿造盛京实胜寺又建了一座藏寺,叫做普静禅林,对外开放,让老百姓拜佛。因为见这里的僧人都戴着黄帽子,北京人便把这里叫做黄寺,就是最早的东黄寺普静禅林。当了皇帝的顺治为了巩固政权,利用宗教把后方蒙古上下人等捋顺,通过金巴嘉措从中斡旋,邀请五世达赖进京,在黄寺西面原有寺庙汇宗凡宇的基础上,扩建成和东面普静禅林一样的藏寺,这座集汉、藏、印度三种建筑艺术于一体的寺庙也叫达赖庙。这就是西黄寺的来历。最早的东黄寺和西黄寺仅隔一堵墙,在同一个外围墙里面,并称黄寺或双黄寺。如今东黄寺已不复存在,此行大家在展室里陈列的一幅1928年日本人的航拍图上还能见到它,说明抗日战争之前应该还在,后来怎么没的,谁也说不清了。西黄寺自1652年建成之后作为皇家寺院,一直是达赖和班禅的进京住锡之处,因此对外界紧闭大门。1987年,十世班禅和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在西黄寺创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自此30年来,西黄寺成为培养藏传佛教界高级僧侣人才的摇篮。一直到2018年5月18日,西黄寺才开始以博物馆的形式正式对公众开放,且只有周六周日可以参观。
北京有句老话,叫“东黄寺的殿,西黄寺的塔”。那么西黄寺的塔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在满足好奇心的期待中,我们沿着正殿后面的一条高台甬道登上3米多高的塔台。回头望去,前方左右各有一座碑亭,黄琉璃筒瓦重檐歇山顶。亭内各竖石碑一座,东碑螭首龟蚨,为乾隆四十七年御笔“清净化城塔记”,碑阳满汉文,碑阴蒙藏文;西碑方首石座,为乾隆四十五年仲冬月御笔“班禅圣僧并赞”,附满汉藏三种译文,碑阳刻玉兰花。再看塔台南面和北面,各有一座四柱三楼通体为汉白玉雕成的仿木结构建筑的牌坊。南面正向的牌坊题额为“慧因最上”,“妙祥真空”;北面居后的题额为“圆觉观音”,“华严海会”。哦,原来占地1.9万余平方米的宏伟城塔,是乾隆为纪念六世班禅修建的。随着“导游”的侃侃讲述,一段历史故事缓缓铺展开来……六世班禅的法名叫罗桑华丹益喜,出生于1738年,即乾隆三年。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受到乾隆厚待,或者说,他有值得被乾隆厚待的优势。为什么呢?简要地说,在17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不丹发生战争,不丹国王请六世班禅写信调解。英国驻印度总督哈斯汀士遂利用这一机会,派遣东印公司职员英国人波格尔擅自闯到札什伦布寺见六世班禅。六世班禅用印度语与他交谈,强调不丹是中国藩属,而西藏属于中国领土,一切都要听从中国大皇帝的圣旨办事。对波格尔提出的英国与西藏建立联系、英方与西藏自由通商、请介绍到拉萨见驻藏大臣并在拉萨设立代表等要求,一律加以拒绝,使波格尔的计划未能得逞。六世班禅地位高、责任大,如此正确行事,堪称模范。为表圣宠,乾隆邀请六世班禅进京庆贺自己的70大寿。1979年6月,六世班禅带着13名勒参巴等随行人员从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出发,马不停蹄地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路程。这一年,年届70岁的乾隆皇帝开始全面系统地学习藏语。在此之前研究佛经时,乾隆已经开始接触藏语。1780年7月,六世班禅到达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看到大清皇帝还能用藏语和他交谈,即惊讶又感动,一番互动,友情加分不少。然而就在这年的11月2日下午,六世班禅圆寂。为什么?六世班禅年纪轻轻,此时才42岁,正值壮年。原来,在前往北京的路上,六世班禅一行住锡青海塔尔寺过冬。从塔尔寺出发前班禅大师让二世嘉木样活佛为其随行人员种痘。不知为什么,他自己却没有种,为以后埋下了祸根。10月下旬,在黄寺住锡的六世班禅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刚开始只是略感鼻塞,以为是鼻炎。后来逐渐厌食,侍膳官发现大师手心脚心出现红疹,怀疑是天花,这才向乾隆禀报。乾隆闻讯十分着急,彻夜难眠。第二天凌晨早早起来,就赶到黄寺病榻前慰问班禅,并命御医诊视,御医同样怀疑是天花。就这样,班禅服药一个多月,11月1号开始发烧,第二天病情突变,黄昏时悄然圆寂。乾隆翌日凌晨一见到大师遗容,泪流满面,痛心疾首地叫道:“朕之喇嘛啊!”当即昏厥过去。为了纪念六世班禅,表彰其爱国爱教的功德,乾隆亲自设计了这座集藏、汉和印度风格于一体的金刚宝座塔。 据说修建此塔没有动用国库的银子,是乾隆自掏腰包。乍闻此言,还真是吃惊。乾隆此举何等用心良苦,不好妄加评判。但是如果从个人情感深厚的程度去看,倒也不难理解。从来没有想到,一个昔日印象中遥不可及、高高在上的封建帝王,此时此刻一下子变得像邻家老伯那么令人可亲可近。
此行最特殊的待遇,是进入到西黄寺不允许参观的教学区阳光楼。只见崭新高大的殿堂式教学楼高端大气,到处整洁明亮。安静的阅览室书香四溢,资料丰富的展览室图文并茂,详尽地展示着学院概况和丰硕的办学成果,令人倍感欣慰。特别是在录像厅观看了VCR,更是激动人心。通过一幅幅真实的资料画面,看到学院30年来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僧才,壮大了藏传佛教界爱国进步力量,大家都发出由衷地赞叹,响起阵阵掌声。
离开西黄寺时正值中午,冬日里一缕缕耀眼的阳光,把天王殿照射的更加金碧辉煌,光彩夺目。不再感叹时间,感慨岁月,因为我们看到了一座万物复苏的古老寺院,一个生机勃勃的年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