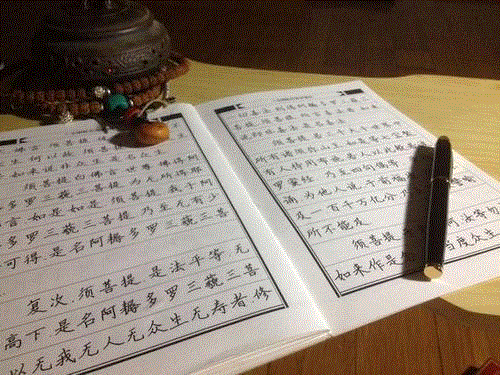《赵城金藏》研究
发布时间:2022-03-24 11:57:34作者:药师经全文
(一)《赵城金藏》的发现
1933年,“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理事范成在山西访经中,在赵城广胜寺首次发现了《赵城金藏》。1934年秋,为详其究竟,蒋唯心赴广胜寺“检校”经卷,并据之撰写了《金藏雕印始末考》一文。经范法师发现,蒋氏检校的《金藏》“依千字文编帙,自天字至几字,凡六百八十二帙。……原藏应有七千卷,今纔存四千九百五十七卷。”《赵城金藏》发现后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三十年代,北平、上海的僧俗学者将其中未经传世的四十六种经论撰述,以《宋藏遗珍》为名影印出版;还将一部《楞严经》按原尺寸影印了四百部,分藏于各大寺院。
(二)现存《金藏》概况
1949年运交北京图书馆的《赵城藏》是四三三〇卷又九大包残卷,以后又陆续有所收藏,到目前为止北京图书馆的收藏总数是四八一三卷。《赵城藏》自发现后多有流散,故地方图书馆亦有零星收藏,据调查这类收藏共四十四卷,其中有流落德国的一卷。1959年在西藏萨伽北寺又发现了三十一种五五五卷金藏印本。北京大学宿白教授因之撰写了《赵城金藏和弘法藏》一文。这部分金藏刷印于蒙哥丙辰年(1256),印成后安置在燕京大宝集寺。经核对,萨伽寺发现的金藏与广胜寺金藏是同一刻本的两种印本,因此我们把这种印本称为“金藏大宝集寺本”,而把现存北京图书馆的金藏称为“金藏广胜寺本”。此外,现存北京图书馆的金藏并不完全是同一印本,其中有金大安元年(1209)的印本,印本上盖有“兴国院大藏经”印章。此印本现存八卷,我们称为“金藏兴国院本”;另有七卷亦区别于多数经卷,我们称为“金藏天宁寺本”。
(三)《金藏》的雕版
《赵城金藏》的发现是现代佛教文献史上的一件大事。金元以来的著作中也有过几条记载,但均被作了错误的解释。如明人陆光祖为《嘉兴藏》作的序中称:“昔有女子崔法珍,断臂募刻藏经,三十年始就绪。当时檀越有破产鬻儿应之者。”此序所云崔法珍即金藏的募刻者。但后人说她是宋《碛砂藏》的募刻者;日本学者则称她为明人,所刻藏经为明《嘉兴藏》。如此误解在《赵城藏》发现之前一直是作为悬案而无法得到证实。
初步统计,现存《金藏》中见于卷尾及版行间的施经题跋约一四〇余条,其中有年代可考者四十二条。这些题跋大致可说明如下问题。
(1)广胜寺发现的大藏经刻造于金代。从四十余处有记年的施资题跋中知道,其刻经时代处在金熙宗至世宗时期(1139~1172),涉及天眷、皇统、大德、贞元、正隆和大定六个年号,前后三十余年。最早的年代是天眷二年(1139),见鸣帙《妙法莲华经》卷三、卷五、卷六、卷七。这四卷经现存上海图书馆,其中两卷卷首有标有“赵城县广胜寺”题字的扉画,说明它们确为《赵城藏》印本。蒋唯心曾提到日本人憍川时雄见过天眷年印造的《妙法莲华经》卷七,但他自己“未见此本”。因此他把《金藏》雕印的最早年代确定在皇统九年(1149),其根据是见于日帙《大般若经》卷八十二的尾题。
(2)这部大藏经是由私人募资雕造的。《金藏》雕刻的施资者绝大多数为晋南诸县村民,涉及县级地名二十余个,比较集中于晋西南解州的夏县、安邑、河津等地。在一四〇余条施经题记中有明确地名而与解州有关的三十余处。据题记,主持雕经的组织称“天宁寺开雕大藏经版会”;此天宁寺在安邑境内。这即是《解州志》所载解州西二十里的静林山天宁寺。就是说《金藏》是以解州天宁寺为中心,由解州所属各县及临近的长治(潞州)、临汾地区及毗邻的陜西个别地方的村民共同施资雕造的。施资者有施财数千贯雕经数十卷的大户,也有仅能施财雕经一版二版的贫苦农妇。有的将自种的树、自织的布、自养的骡,甚至一把雕经的刀子作为资产奉献出来雕造经版,充分反映了晋南信佛教的百姓雕经的热情。
(3)是谁首倡并组织了这一庞大的雕经事业呢?这就涉及崔法珍其人。事实上崔法珍的事迹并没有被史书淹没。《永乐大典》卷四六五〇有如下记载:“弘法寺在旧城。金大定十八年(1178)潞州崔进女法珍印经一藏进于朝,命圣安寺设坛为法珍受戒为比丘尼。二十一年以经版达于京师。二十三年赐紫衣弘教大师,以弘法寺收贮经版及弘法寺西地与之。明昌四年(1193)立碑石。”此记载指出,崔法珍为金代潞州人,她确曾集资刻过一部大藏,并将印本及经版进奉朝廷,经版收贮在燕京弘法寺。现存《金藏》的施刻题记中涉及潞州的近二十条,刻经范围均为重要的大乘经论,说明地处晋南的潞州是《金藏》雕造最积极的赞助地区。我们有理由说,在同一时期由崔法珍向朝廷呈送的大藏经只能是晋南百姓共同雕造的《金藏》,而它的首倡者就是潞州人崔法珍。
(四)《金藏》的补刻
《金藏》经版安置于弘法寺后,在金代有记载的印经活动至少有过两次。时至元初,由于经版部分损坏而进行补雕。补雕《金藏》在现存《金藏》题记中有明文记载,蒋文对此亦有详尽考证。问题是补雕的年代。从《金藏》题记中“宣差大名府路达鲁花赤纳邻蒙古提举补修雕造”一语看,补雕《金藏》事当在1224至1271年间。《金藏》题记中见于这一时期有记年的题记还有六则,其中四则为壬寅年(1242),另有戊戌年(1238)一则,癸卯年(1243)一则。这说明补雕《金藏》最集中的年代应在1242年前后,此时正值元太宗执政时期。这与《至元辨伪录》卷五中“太宗则试经造寺,补雕藏经”及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所录“补大藏经板疏”诗所表述的年代大体相合。然而发现于河北曲阳的一则〈觉辩大师源公塔铭〉云:“都城弘法寺补修藏经版,以师为提领,三年雕全,师之力居多焉”。此铭文撰于“大朝戊子岁”。据收录此铭文的《曲阳县志》推算此年为金正大五年(1228),即成吉思汗去世的第二年。是年其四子拖雷监国,元太宗尚未立汗。此塔铭指出了元初补雕弘法《金藏》这一实事,但把时间说在元太祖之时,且已完成。这与现存《金藏》的实际补雕年代不符。我认为这不是铭文的错误,而是推算者的误识。据铭文,觉辩坐化于丙午年(1246),塔铭不可能立在觉辩去世前十八年,因此“戊子岁”应是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此年虽距觉辩死已有四十二年,但后人在先师故去数十年后为其立碑事还是有过的。

(五)《金藏》的校补与《弘法藏》
《金藏》补雕后曾有印本行世,此即金藏大宝集寺本。此本何以会运藏西藏,这里不再详论。大宝集寺本刷印于蒙哥丙辰年,说明补雕《金藏》在蒙哥时代已经完成。这样,就又有了一次校补问题。《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载:“弘法寺藏经经版历年久远,(世祖)命诸山师德校正讹谬,鼎新严饰补足,是传无穷。”对此宿白教授文中有专门论述。他认为元世祖主持的这次《金藏》的校补,首先是增补了“弘法入藏录及拾遗”,编入的经律论七十五部二五六卷;其次是“蕃汉对勘”,并指出“至元录即世祖校补弘法旧版后之详目,亦即元弘法藏”。我们据此与现存《金藏》作了核对,发现《至元录》与现存《金藏》并不是一回事,出入很大;《至元录》中所云弘法入藏录也与现存《金藏》有相当差异。对此作何解释呢?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这次校补不是据弘法入藏录进行的;再一种可能是确有一种新的弘法大藏的雕造,其目录即弘法入藏录。日本学者小野玄妙就持这种观点,这与宿白教授的观点不同。小野所云《弘法藏》是在弘法旧版基础上重新雕造;而宿白教授所云《弘法藏》则是弘法旧版的增补。《弘法藏》问题不是现在才提出的,元至顺三年(1332)吴兴妙严寺所刻《大般若经》卷一的题记中已有“大都弘法”之称。如果是重新雕造,在弘法寺就会同时有两副大藏经版,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第一,如果是重新雕造必为官版,其刻造年代当在元世祖校补《金藏》完成的至元二十四年(1287)前后,其经版不可能在短期内损坏。然而就在此后不到二十年的大德年间,京师高僧溥光传只知“藏经板本在浙右”而不知或不重视在京城有《弘法大藏》事,说明《弘法藏》绝非新雕官版。第二,有确凿证据说明在世祖去世不久的元仁宗至文宗年间,元官方确曾新雕过一部官版大藏,版贮官署金王府。近年发现于北京智化寺的几卷元藏就是这种藏经的残存部分。我认为,所谓《弘法藏》就是经元初补雕的《金藏》,只因历时久远,人们已不了解它从晋南运藏弘法寺的这段历史;加上缺少检校之人,使《金藏》的雕印史鲜为人知,故世人只知有大都弘法而不知有崔刻《金藏》。也因弘法经版残损严重,虽经校补仍难以官版面世而受到冷遇,故此在世祖去世后元政府又进行了一次官版大藏的雕造。再拿《至元录》与智化寺元藏比较,发现二者十分接近,而《金藏》与《至元录》相比,编次相差五十余字。很显然世祖命诸山师德校补弘法经版,目的是要编辑一部权威性的官版大藏,但未能实现,只编了一部《至元录》。这一愿望在仁宗至文宗朝才得以实现。现存《金藏》在中统三年(1262)即已运至赵城,说明它与世祖校补弘法《金藏》关系甚微。
(六)《金藏》的底本
蒋文云:“崔氏刻藏最为一目了然之特色者,即在覆刻北宋官版大藏经。”这是数十年来学界推崇《赵城藏》的主要原因。《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刻本大藏,现仅存十三卷。《开宝藏》全貌只能从《开宝藏》刻印后留下的资料来推断,其中当数成书于宋崇宁三年(1104)的《大藏经纲目指要录》。这是惟白阅《开宝藏》所集的一部提要式著作。我们将现存《开宝藏》与《指要录》核对,帙号无一差错。拿现存《金藏》与《指要录》对照,它们无论在帙号、分卷及内容方面几乎完全一致。在重编《中华大藏经》过程中遇到一些难以解释的疑问,如《金藏》的千字文编次在《大般若经》后与宋元诸藏均异;晋译《华严经》诸藏为六十卷本,《金藏》为五十卷本。按照一般的情况应查对《开元录》,但《开元录》在上述问题上与宋元诸藏同,《指要录》却与《金藏》一一吻合。这说明《指要录》是《开宝藏》的实录,而《赵城藏》则是《开宝藏》的覆刻藏。《指要录》止于“英”帙,与《金藏》“天”至“英”四八0帙的内容全同,这是《开宝藏》初雕本的内容。《开宝藏》初雕本完成后的一百余年间陆续有所增补,如惟白所述,当时的“官印版”又增加了经传三十帙和未入藏的二十七帙。现存《金藏》的个别经本中留“大宋咸平元年(998)奉勒雕造”、“绍圣二年(1095)雕造”及大宋景德元年(1004)、天圣三年(1025)、六年、九年等原雕经题记及译经、讲经题款,表明《开宝藏》的续刻持续到宋哲宗年间,而这百余年续刻的内容亦已反映在《金藏》中。现存《金藏》“杜”至“毂”帙的北宋新译经即惟白所云经传三十帙;“振”至“奄”帙的宋以前翻译经论即惟白所云未入藏二十七帙。此外金藏收录的“岫”至“亩”帙的天台宗著述及“我”至“劝”帙的法相宗著述是宋仁宗天圣四年敕命“编联入藏”的;“起”帙以后的其它史传著述亦有奉敕入藏的记载。总之,《金藏》是《开宝藏》的覆刻藏是毫无疑问的。这不仅在内容方面,在版式上亦可作印证。现存《金藏》前四八〇帙及续刻的经传三十帙和未入藏二十七帙均为卷子装,每版二十三行,每行十四字,这是《开宝藏》原式。至于其后的其它著述类典籍则多有不同,有的与发现于应县的《辽藏》极似,有的与福州版大藏相近。此种情况是反映了《开宝藏》原貌,还是另有原因,尚难论定。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典籍中有相当部分是未经传世的孤本珍品,说明《金藏》内容在《开宝藏》基础上又有新的突破,从而使它的收经总数达到七千卷之巨。这是宋元时代其它任何大藏所无法比拟的;这也是我们选用《赵城藏》作底本重编《中华大藏经》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