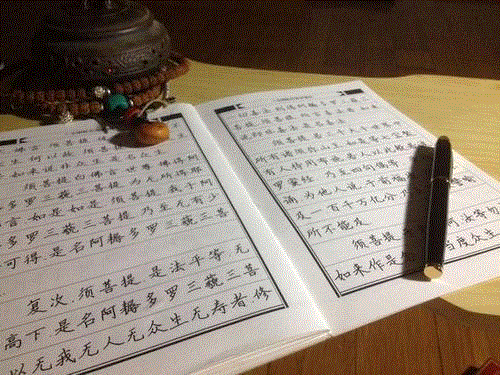洋和尚照空
发布时间:2022-11-04 09:52:45作者:药师经全文洋和尚照空
巨赞法师
一、照空受戒记
1931年3月,我在杭州灵隐寺削发出家。我的师父却非方丈要我不一定马上就受戒,而太虚法师以为非马上受戒不可,我就和太虚法师同到上海,在赫德路净业社住了两天,又转南京。那时他是中国佛协会主席,以他的名义,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我带着,赶到离南京四五十里的宝华山隆昌寺去受戒。
到隆昌寺是3月11日,已经“封堂”(宝华山每年传戒二次,春期自3月1日起至4月初8止,凡受戒者必须于3月1日前入戒堂,过期不收,故名封堂)。过期十天,照规矩是无论何人一概不收的,也从来没有破过例。可是太虚法师的介绍信为我开了方便之门。当家师招呼得很周到,兴高采烈地告诉我有一个外国人也在受戒。我淡淡地问:是不是印度人或高丽人?他赶紧说不是,是西洋人,不会讲中国话。我心里非常奇怪。
当家师陪我吃了中饭,引我曲曲折折走到韦驮殿左边楼上,靠近山门口的一间房里去。窗前一个身穿灰色布衣,头上剃得光光的戴眼镜的和尚,伏在桌上用自来水笔写字。他见了我们,站起来向当家师合十作礼。呀!高鼻子,绿眼珠,他就是那个受戒的西洋人!我再不能抑制我的好奇之心,就操着不甚娴熟的英语问道:Maylspeak EngUsh With y。u?
他慌忙卸下眼镜,和我攀谈,我才知道他法名照空,匈牙利人,生长在德国,五十二岁。还有他的师父寂云、师兄照心也在此。当家师把我安置在他的对面铺上,他很殷勤照拂我这个新来的“戒兄”(同受戒者以戒兄互称,我们则互呼br。ther),叠被铺床,又借了一条毛毯给我盖脚,说:虽然春深,山上夜里还是很冷,一不小心就感冒,对于受戒是不大方便的。
过一会,他的师父、师兄进来了。他首先把我介绍给他的师兄,原来是他的义务翻译,六十岁,广东番禺人,据说是海军界的老前辈,美国留学生,俗名庞子扬,参加过中东之役,又帮黎元洪在汉口办过武备学堂。后来我们熟识了,他告诉我许多关于黎元洪和宋教仁的事。他说宋在当时不过是一个学生,而学潮来时,教师解决不了的,必挽宋出来转圜,故共称之为宋公明。照空的师父是浙江天台人,年纪比他小,日本留学生。未出家时,在官场中混过,和陈英士关系很深。长方脸,络腮胡子,衣服破破烂烂,望之令人生畏。我们四个人住在一起。
他们都不吃晚饭,因为寂云和照心同在泰国的佛教团体里住过,而照空,据说在锡兰的庙里学过二、三年巴利文和梵文,所以都还保持着南方佛教生活的习惯。我也就跟着他们每天只吃两餐。不吃晚饭,佛教术语叫作“持午”。头几天,我有点过不惯,五六天后,早午两餐的分量加多,也就不觉得什么了。而照空替我记下了每餐逐渐增加的碗数,这使我非常惊异。
当时受戒者男性共四百余人,除我等三人住于客房外,其余皆分住四堂,每堂有堂师四人,分司教导戒规之事。照空、照心隶第二堂,我隶第四堂。堂师非常优待我们,每饭必添菜,尤其是红烧党参苗,我最爱吃。所以人家排着班在斋堂里捧着钵,肃静无声地呷豆腐汤,而我们食前方五尺——半个方丈——比出钱的施主还吃得好;并且不要半夜起来作早课,晚上也不要在韦驮殿里叩几百个头。有时人家在搬柴、摘茶叶,佛家术语名之曰“出普”,而我们却荡着手游山。在那几百张面孔的表情上,可以看得出对于我们的羡慕之深。
我因为到得迟,有许多规矩没学到,如拜佛,搭袈裟,开坐具等等的方法,都是照空转教给我的。我问他出家的原因和在俗的姓名,他告诉我,姓Linc。ln,名Trebit。ch,对于佛法有真切的信仰,不吃肉已很多年,又因为受了爱子瘐死英伦的刺激,所以出家。后来照心对我说,照空当过吴佩孚的顾问。因和照心的儿子熟而认识照心,又因照心而认识寂云。照心陪照空在杭州城隍山准提阇——寂云的小庙里住过一两个月,就在那里决定落发。照心为着成全这第一个在中国出家受戒的欧洲人,也决定出家,自己和寂云于是由朋友而变成了师徒。
戒堂里并不清净,尤其是中国人不讲究卫生和堂师们的无知无识,使这个欧洲人不十分满意。大约是快要受比丘大戒的时候,他那一堂的堂师,任意用细杨枝在受戒弟子的光头上敲着教“遮难文”,激起了他的无名火,他对我和照心说,这样野蛮,非但不合佛法,而且也不是人对人的举动,他不受戒了,要到南京去告他们。我和照心极力劝阻,又请知客师出来转圜,叮嘱堂师们以后在照空面前,不要用杨枝打人,他才答应继续受戒。传戒和尚德宽,有一次请他去谈论这一件事,是我陪去的,大家看见我和他同来同往,就将一切是非归罪于我,当家师固然不高兴我,堂师们每餐的添菜也没有了,照空轻藐地骂那班和尚可鄙。
照空说,受戒以后,准备到法国南部建造一个佛教丛林,大体的规模采取中国式,内容则注重学术化,不是有相当学问的和尚不挂单,要我去帮他的忙。我答应了,约定到上海去商量。这时江宁昙的昙长听说有西洋人受戒,特地来参观,和照空谈了许多话,偶尔说了一句“四大皆空”,照空就钉着问四大从何空起?那个昙长虽然在美国读过书,并没有研究过佛学,回答不出。照空回来要我问他的师傅,寂云说,本来是空的。我翻译给他听,他摇摇头,“n。”了几声。我问他怎样回答,他说四大从我空起。
他又说,英国的哲学家,除Hume差强人意外,其余皆不是道,乃是英国文字不够表达高深思想的缘故。德文文法和梵文很相似,近来直接从梵文译成德文的经典很多,而且很靠得住,所以他深以生长在德国为幸,而且劝我学德文。此外他又写了两个懂得外文的锡兰和尚的名字和通讯处给我。这是我随身带的Ruskin和Carlyle的书引起来的话。
四月初一早晨吃糖糯米粥,所有的红枣子,都被照空一个人舀去了,他说是G。。dOmen,因为那天是他第三次到中国来的一周纪念日。他又说,匈牙利人就是匈奴的苗裔,在全欧洲也只有匈牙利人衣服上像中国人一样用布扣子,所以他相信他的前生是中国人。下面两个故事,是他那时告诉我的。
不记得是民国几年,照空在汉口替某方活动,于花柳场中认识一个姓王的经理,征花纵酒,天天在一起。有一次,叫到一个年约二十二三的歌女,举止很大方,谈吐也不俗。姓王的还是那一股轻薄劲儿,照空劝他放尊重点,当时那个歌女很感激似地请照空明天到她的芳居去耍。照空觉得她懂英语,就用英语问她,她摇摇头,装作不懂。第二天他如约而去,刚进门,听到弹得很熟练的钢琴声。琴声止,歌女含笑出迎,在她的妆台旁边,发现有一本狄更司的原文小说。照空就凭着这个强迫她用英语和他谈话,她的确懂得英语。照空恳切地问她为什么自甘堕落,她流着泪,向照空诉说生平。她是满族人,辛亥革命时,父亲和哥哥在杭州自尽,她和母亲逃到上海。不上两年,典当殆尽,日子眼看过不下去了。那时她只有十四五岁,她恳求她的母亲把她卖出去,终于卖给了鸨母,鸨母见她知书识字,相貌出众,很想把她栽培成摇钱树,英语和钢琴就是那时学的。到了十八九岁的时候,广东的曹某恢复了她的自由,同她正式结婚。谁知同居不久,又被遗弃。她的母亲为此气病,不上一年就死了。她那破碎的心,还痴想着在风尘之中,物色个诚实君子,托以终身。照空问明了那个姓曹的名字,原来是和他相熟的,他出于慈悲,极力斡旋,终于弥补了这一片情天的缺陷。
还有一次,在京沪车中,一个美国人对着几个初到中国的英国人大骂中国是匪国。照空声色俱厉地对那个美国人说:“我在美国的时候,有弟兄两个抢了一列火车。强盗在闹市里假装拍电影外景,抢了刚从银行里用汽车运出来的几百万块钱。这是大家知道的事实。中国的土匪,和美国的比起来,不过是些顺手牵羊的小偷而已。”接着一个英国人就向他请教中国问题,一个日本记者也插进来问中日怎样才会协调?他说:“中日的不协调是日本人造成的,只有日本真能开诚布公和中国合作,中日之间的冲突,才能解决。”那个日本人偷照了他的相,后来他经过日本的时候,发现那张相片和新闻一起在报上登出。
四月初八是释迦牟尼佛的诞辰,我们就在这一天受菩萨戒。燃香或称烧疤,是用以表示学佛决心和牺牲精神与供养心的。唐代苏鹗的《杜阳杂编》、宋代王君玉的《续杂俎》里所记的“练顶”,就是这个制度的作俑,在受戒当中是最后的难关。用艾绒做成的半寸长的香,虽说已经烧存了性“’,重新点起来也还要半分钟,尤其是要把火灰按在头上,最是难受,每次总有几个被烧昏过去。但是我们又受到了特别的待遇,这是我永远忘不了我们那位堂师的地方。因为他在火刚要烧到头皮上,我感觉着如针头刺痛的时候,他就很快地把火灰一个个拿掉,手法之敏捷,真是少见,过后虽然有些热辣辣不好过,可是并不痛苦。照心怕溃烂,想用万金油搽。寂云说,搽了油就没有疤,照空也表示不赞成,说疤是区别僧俗最好的标志,将来他到法国开丛林,传戒的时候也要用这办法。
这时。太虚法师特地寄给我一封信,要我受完了戒不要下山,就在隆昌寺住。我和照空商量,他劝我只当没有接到那封信,一同下山。关于住的问题,寂云说,只要不嫌淡薄,到他的小庙去住没有问题。于是我就和他们三人及另外许多戒兄下山同到龙潭。我因为所有的行李都在中国佛教会,故先回南京,他们则先到上海,约好一星期后在上海古拔路一个德国旅馆里见面。
到了南京,太虚法师劈头就问,收到他的信没有?我惊讶似地说:“什么信?没有!”这是照空教给我的。于是太虚法师把那个递信的老实人责怪了一顿。当时太虚法师因为和圆瑛不和,打算辞职不干了,要我和谈玄、如明两人组成佛教宣传考察团,首先去安徽工作,并且说,如果我不参加,他们也不干。因为当时谈玄还写不通文章,如明虽去过德国,但笔墨有限。我替他们拟好了简章和备案的公文后,就带着一部分日常用品溜到上海。照空正准备到北平去,寂云、照心则已经回了杭州。我在那小小的德国旅馆里只住了一晚,关于到法国南部建造佛教丛林的事并没有谈到。第二天他搭车去北平,我搭杭车回杭州。
到了杭州,才晓得照心虽为照空而出家,但对他并不满意,他们师徒之间,有老大的裂痕。没几天,照心愤恨地回香港去了,寂云有事要问照空,还得由我转述。最奇怪的是,还有伦敦Buddism in England的编者March君,要我转寄给照空的一封信,大意如下:
……我早就想写信给你,总没有写成。前几天有一个朋友在柏林看见了你的大着War can be ab。lished,写信来问我关于你的种种,我替你答复了他,现在来告诉你。
关于你出家是否真心实意的问题,我的答复是“一个刚从黑暗里出来找到光明的人,我想不会再到黑暗里去的”。
关于你受戒时,是否在头上也要野蛮地烧上几个疤的问题,我答道:“既在中国受戒,当然要烧上几个野蛮的疤,何况又是到西藏去的绝好护照呢!”
我把这封信转寄给照空,一直没有得到他的信,消息从此断绝。
二、照空的师父
寂云俗姓谢,名国梁,号仁斋,浙江天台榧溪人。早岁留学日本,攻法政。回国后,在东三省做过官。家里本来很殷富,自奉甚厚,食非肉不下箸。后来去向弘一法师请教,因而茹素学佛,独资造极乐寺于天台苍山之麓,供养弘一法师,但弘一法师只小住数日就他去。后寂云与尤惜阴、庞子扬同去泰国,在那里住了几年。尤惜阴在南洋出家,法名演本,号弘如。寂云回国后,经过厦门,于1 9 30年从南普陀寺的转逢老和尚剃度,法名寂云,号瑞幢,是年冬即去南京宝华山受戒,并定居于杭州城隍山准提阇。准提阇本来是一个很小的香火庙,寂云接住后,在其东侧空地上造了五六间静室,作为同道们修学之所。我回到杭州,就住在准提阇的楼上。到年底,听说寂云的皈依弟子之间发生了意见,我就离开准提阇到以梅花着名的超山去住,此后就没有再见到他。1 956年6月1 7日,他从四川寄给我一封信,已经改名为“了性”了。信的全文如下:
老拙自在杭别后,不久辄去结茅终南。迨抗日军兴,乃携钵入川,寄居荒寺,农园自给。日寇投降,拟朝峨嵋后东归。道经嘉定,被诸居士留住,忽忽又六七载矣。前日阅报,知京中有佛学院之筹设,闻讯之下,欣喜莫可言。当此大法绝续之秋,凡为佛子,皆应努力,随时代而改进。拙虽老病残年,亦思奋勉,岂可沉寂空山。因之不揣冒昧,肃笺敬恳座下可否为之介绍,加入僧团学习服务。倘获依处,得亲善知识,幸何如之。待宝成路通车后,便可带一随侍能耐劳苦之青年新戒,准备北迁。有无机缘,务望拨冗赐复,鹄候慈音。
寂云禅师高年博识,对于开办佛学院,如此热忱,使我十分感动,当即寄去川资,请他东下。可惜,不久就得到嘉定方面佛教界来信,他因住山多年,感受风湿,心脏病发作逝世了。他的遗着有《农禅诗钞》一册。
三、照空想去西藏被阻于重庆
据1931年7月世界新闻社报道:前国际侦探、英国会议员、耶教牧师及油企业家林肯氏最近在中国为僧,完成了出家仪式。此事引起一个问题,即西方人归向东方的宗教,已经到达如此热烈的程度,原因究竟何在?因此,E.Uanter氏曾走访照空于北平城中荒僻处的一所中国式房屋中。照空把他头上的十二个香疤给他看,证明他已经变为中国的外国和尚了。他全身都是僧装,布衣布鞋布裤,纯为中国材料所制。他说:
我在中国出家,就是对此世界已不复感有兴趣了。我今年五十二岁,世味备尝。张眼看此世界,看不到别的,只见苦痛与烦恼,而一般人如醉如狂,沉溺其中而不悟。
我自入世以来,也曾和大家一样努力求快乐,我也曾经一度为耶教牧师。然对于耶教,愈研究愈减少信心,终于脱离耶教。既而图求教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尼采及叔本华,又求乐于金钱名位,然而愈求而失望愈多,余开始觉到生活真是一种惨剧。因此厌弃世间,转而为僧。
他说,他已不复注意政治,往往数星期不看报纸。他又说,国民党政府曾因德国军事顾问鲍欧氏的介绍,拟聘他为政治顾问,他没有答复,鲍欧曾批评他“愚不可及”。他到北平后,曾发表过《我为什么出家为僧》一文,兹节录其中数段如下,以见一斑。
一切生命,抱同一个目的,神与人,禽兽与草木,一切皆然,绝无例外,一句话,就是试图快乐。所以乐的问题即是生的问题,生的问题也就是乐的问题。

吾人求乐之道,虽各各不同,而以满是欲望为乐则无不同,由此可见吾人所追求者,实属同一。吾人自呱呱堕地到撒手长眠,无一时不如此,其间从无改变,也不能有改变。但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得到真正永久之乐,这是不可否认的。因而人们构设一切幻想以遮掩之。
目前,德国的若干学者,继法国学者之后,认为基督《圣经》包括《新约》在内,不是以使人信服。同时在锡兰、印度工作的若干英国人,因为接触了《吠陀》经典与佛教,感到非常有味,尤其是佛教。遂不畏艰难,从事学习梵文及巴利文,首先译佛典为英文。英德两国均设有巴利经典会,其目的在于把巴利文经典翻译刊布于世。经多年的辛苦工作,巴利经全部已在英国刊布了。
今日的西方世界,对于佛教的兴趣及了解,正在日渐滋长。德国柏林附近有一所佛学院,系已故的丹律克博士所设。在汉堡、莱伯锡、特来斯登,均有佛教团体。在慕尼克有一个佛教会,主持者乃西方最伟大的佛教学者葛立穆博士。慕尼克佛教会与法国南部的一个佛教团体有联络,这个法国的佛教团体是我去年游法时所组织的,其总部设在尼斯。英国佛教会有多处,在伦敦附近有一佛寺,乃锡兰僧人于两年前募建的。美国也有佛教团体若干。而佛教刊物,则英、德、美三国都有。
中国及中国的佛教徒应派导师到欧洲及美洲,用佛说的真理教导其人民。教彼等以达到和平快乐之路,教彼等应作善而勿为恶,教彼等求生命之真理,勿妄信幻构之天国。
从上述照空的自述看来,他出家是有深刻原因的。可是他研究过南传佛教,没有接触过中国所传的佛教,尤其对于中国佛教的现状,毫无所知。据l 934年《海潮音》五月号法舫写的一篇文章中说:
忆在北平时,余曾请照空在柏林寺讲演,其所说的道理,纯属小乘佛教,曾蔑视中国无真正之出家僧人,表示彼将传道于中国。当时中外僧俗听众五六百人,颇有不惬意者,余即宣告:
“照空所说不能代表整个佛教,更不能代表中国佛教,他所说的不过是少部分的小乘佛教耳。他如果要在中国传教,希望他息心在中国居住十年研学中国佛教。”听众颇以为然。后来,我又约胡子笏、汪波止、林黎光诸人与照空谈话,现将该谈话情况录要如下:
“照空师,你到中国有几次?”我们问。
“前后共六次”他回答。
“未出家前,研究佛学有几年?”
“与佛学接触有三十年之久,但是专门的真实的研究,是最近的六年。”
“研究佛学所取材料是何种译本?”
“大多数是巴利文的德文译本,间及巴利文的英文译本以及日本人的英文写本。我看这几种译本佛书时遇着难题的时候,便直接去研究巴利文,但我对巴利文,亦未深通。”
“照空师,你曾与中国出家、在家的佛学者谈过佛学没有?”
“没有,我从没有看过中国佛书,也没有与中国佛学者谈过佛学。”
后来照空又说:
“我对于佛学唯信仰‘佛说”\’’的才认为是真的,不信其他的东西,如像中国的偏于大乘和锡兰、印度的偏于小乘,我一概不相信那些大小乘的佛经。那些不是真实佛经。佛经没有大小乘的,须知佛在世本无大小区别,也没有写出各种经书来。《四阿含经》里包含佛说很多,所以我不相信佛法有大小乘的分别。”
“你不相信有真的佛经,那么,你的佛学知识,从何而来?”我们又问他,,
“我也不完全说一切经典都是假的,我也相信有很多的圣典是真的可学的,不过其中有很多是错的。但是依着惟一无二的一个方法,也容易知道哪部经是真的,哪部经是假的。”他回答。
“依何种方法得知?”我们问。
“无我,凡与无我道理相应者为佛说,否则不是佛说,,”他的回答。
“我们知道无我这一点,在中国佛学上,是所谓三法印之一,是佛教大小乘法的共同原理。还有两个法印,你全不知道。”我们最后对他的回答。
如此不断地谈了是有一小时半才结束。我们认为他对于巴利文小乘佛学,似稍有相当的研究,未必全部洞悉。不过他认识佛教“无我”的原理,那是《艮对的。其他的话,不过是观察不同,他有先入为主,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我慢主观罢了。
照空在当时的北平如此演讲,当然不受欢迎,还有化名“不空”的人,着文大加攻击,照空就离开北平,到达重庆。
从上述英国March君给照空的信看来,照空本有去西藏研究佛教的打算,他到重庆,就是去向刘湘提出帮助他去西藏的申请。刘湘是个军阀,当时他非常注意西康和西藏的问题,又正支持开办汉藏教理院的事情,对于照空的申请,顾虑重重,非但不予答复,还把他安置在北碚缙云山上的寺院里。照空在那里住了一些日子,知道此路不通,就出川离开中国返回欧洲。
照空师徒是在1 93 5年初回到我国的。及至日本军队进入华北,照空到了上海,听说日寇开始想利用他,他坚决拒绝,并曾写文章发表在欧美的报刊上,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日寇就想对他下毒手,他曾和一个徒弟带着一点资财,潜往后方,但半路上被国民党军劫掠无余,他又不得不重回上海。
1943年10月8日,六十四岁高龄的照空,因手术逝世于仁济医院。其葬礼举行时,有各国人士参加,安葬于上海第一区公墓。有人说,照空在手术中逝世,是日寇下的毒手。